程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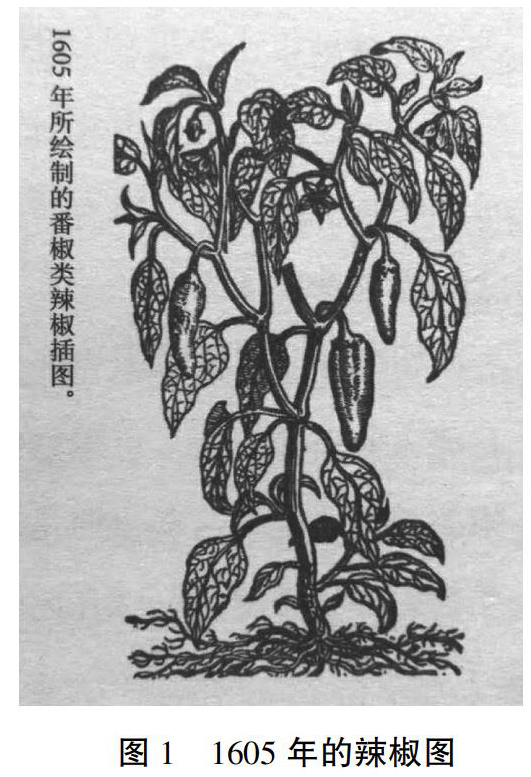
摘要:我国最早记载辣椒的文献不是明浙江高濂《遵生八箋》,而是山东王象晋《群芳谱》,地方志最早的记载也见于山东。我国辣椒发源于山东,入清后由此向北、向西逐步传开,所用名称主要是秦椒,在整个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时间连续、名称大致统一的传播区。康熙、乾隆年间,以华北平原为核心,包括山东、辽宁等地方志的辣椒记载相对密集,是我国最早的辣椒喜食区。康熙至道光年间,我国南方的辣椒从浙江发轫,时间稍晚于山东,最初多称辣茄,台湾、福建一线后来传入的品种则称番姜。整个华东地区早期地方志记载比较稀散,显示出大致相同的区域特征。中南、西南诸省区的辣椒记载更晚一些,但大多比较密集,传播过程有着紧密联系。其中湘西的辣椒记载早、分布密,最初多称海椒,应该来自广东沿海,深得苗、瑶等少数民族生活风习传布和“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推动,又适应一些缺盐、瘴湿环境民众的特别需求,由此先后向南、向西强劲传播,最终形成以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为核心的广大密集分布区。四川盆地的辣椒兼得南北两个方向的来源,有着南北两路终极汇流的色彩,也标志着辣椒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传播主体过程的基本完成。上述三大区固然起始时间有先后,但更多是辣椒名称、传播关系、分布疏密的不同分野,奠定了我国晚清以来辣椒不同食用习性的区域格局。根据上述辣椒起源、传播情况及相关品种信息,可将我国古代辣椒的传入分为两个阶段。最早的辣椒应来自与山东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传入时间在明万历后期。辣椒这样的茄科草本植物在我国以木本之“椒”命名,应与最初落脚在传统秦椒分布较盛的山东有关。清康熙尤其是乾隆以来,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东南、华南沿海及相邻的江西等地多有不同新品种陆续记载并逐步内传,其来源则应以东南亚为主。
关键词:辣椒;美洲新大陆作物;秦椒;《群芳谱》;《遵生八笺》
中图分类号:$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0)03-0103-24
作者简介:程杰,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我国辣椒由美洲新大陆作物传入,对传入我国的时间以及在我国的传播过程已有不少学者参与讨论。就笔者所见,近20年来,蓝勇、蒋慕东、王思明、丁晓蕾、胡义尹、侯官响、郑南、俞为洁、刘夙等学者发表了不少可贵的论述。2018-2019年,笔者因偶然机缘触及这一问题,产生了一些疑惑,遂着力就我国辣椒起源、传入途径以及早期传播状况进行深入考索和梳理,全局和细节都获得了不少新认识,不揣浅陋,一一奉述如次,就教于诸方家及广大有兴趣的朋友。
一、我国最早的辣椒记载不是《遵生八笺》而是《群芳谱》
今人论及我国辣椒的起源,多举明高濂《遵生八笺》卷一六“番椒”:“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子种。”该书卷首高濂(1527-1596,浙江杭州人)自序及屠隆(浙江鄞县人)序写作时间均署“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1591)。论者一致推为我国文献记载辣椒之始,并相应形成辣椒由浙江等东南沿海传入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遵生八笺》的“番椒”内容不出于万历十九年
笔者考证发现,南瓜是最早传入我国的美洲新大陆作物,最初出现于北京、河北一带,应是明正德末年葡萄牙使者作为观赏植物种子带到北京,由皇家苑囿种植流人民间。为此对李时珍所说“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作全新解读,并阐明今人相关论述的严重错误。为慎重起见,选择同为新大陆作物的辣椒作为参照。因辣椒在新大陆作物中食用价值并不突出,果实鲜红,观赏性相对鲜明,故有可能与南瓜同时传入,最早也应出现于北京一带。但今人论述多称最早出现在浙江,这不够合理。如果不是皇室交往的特殊渠道,纯然由民间自然传种,进入我国应不会如此迅速。这不能不使笔者对“万历十九年(1591)”这个时间油然生疑。另外,记载中所说“丛生”,与辣椒生长状态明显不合,也值得怀疑。于是不得不认真追索,果不其然,这个所谓最早记载的时间和内容都存在问题。
问题出在文献学上。今所见《遵生八笺》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明万历十九年序刻本,每卷标“雅尚斋遵生八笺”,通称雅尚斋本。雅尚斋为高濂别号,该本应是初刻本,是高濂实际所撰内容。二是弦雪居翻刻本,卷端题“弦雪居重订遵生八笺”,编者署“景陵钟惺伯敬父校阅”,多为清嘉庆以来刻本。钟惺(1574-1625,湖北天门人)字伯敬,生活时代晚于高濂,所谓钟氏校阅应是书商托名促销而已。两种版本正文内容有些细节不同,比如“番椒”这条雅尚斋本无,而见于弦雪居本。后者传刻较多,成了通行易见之本。今人整理《遵生八笺》,实以弦雪居本为依据。如巴蜀书社1988年版全本《遵生八笺》,虽未交代所据版本,仅就其中《燕闲清赏笺》部分来看,属弦雪居本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赵立勋等《遵生八笺校注》,卷首《校注说明》称“选定明刊雅本为底本,以崇祯刻本和弦本为主校本”,凡底本不误,“概以底本为准”,凡有改动,均“予以出校说明”。这个校勘体例定得很科学,但全书成于多人之手,疏严不一。笔者逐条核查,卷3至7基本按此办理,而卷9、12、15、16、19都有不少条目,甚至是大段弦本新增的内容径录不注,实际使用的是弦雪居本而非雅尚斋本。“番椒”这条正在第16卷,该卷弦雪居本多有增补。弦雪居本按照雅尚斋本翻刻,绝大部分页面文字起始、分行都完全相同,如有少量增补,多以小字加注的方式增入。如该卷“枳壳花”“红蕉花二种”题下小字、“挂兰二种”条末小字都是在原版空白处增刻的。如有进一步增添,为了不影响下一页的版面,就把当页条文中语句混乱不爽的内容删除,换刻等量的文字。卷16“番椒”条就是由同页“山茶花六种”条删去一段文字腾出两行后补进的。而校注本对弦雪居本这些改动都全盘照收,且未加任何说明。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版王大淳等整理本同样称以初刊雅尚斋本为底本,以弦雪居本为校本,但基本采用赵立勋校注本的成果,至少《遵生八笺》第16卷的正文部分完全一致,也未见任何交代。今论者引用《遵生八笺》“番椒”资料,应是仅就所见这些现代出版物提供的文本,将写作时间定为万历十九年,未注意版本之异,导致相关判断和论述不能无误。
(二)《群芳谱》所说“番椒”是我国辣椒的最早记载
也许是受万历十九年《遵生八笺》始载辣椒这一说法的影响,不少论者经常连带提及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所说“辣椒花”,也视其为较早的辣椒信息。《牡丹亭》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戏文中有一段插科打诨,末角举“辣椒花”,净则附和:“把阴热窄。”意思是说辣椒花能祛除阴湿之气。笔者以为,唐《初学记》辑有“晋刘臻妻元日献《椒花颂》”的掌故,杜甫《杜位宅守岁》中有“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之句,以后椒花就成了诗文常典。明时蜀椒、秦椒之类已多称花椒,因花椒味辛而称“辣椒花”,是戏中角色随口凑成三字花名以打趣,不能视为指今日所说植物辣椒的花。想必在明朝,即使万历十九年辣椒已引入中土,辣椒花是否立即用作药用,广为人知,值得怀疑。辣椒开细小白花,极不起眼,是否能引人注意,用作戏文说辞,更是值得怀疑。其实“辣椒”一词在时间更早的沈周(1427-1509)《石田杂记》即已出现,称“造红曲法:先取辣椒,不拘多少,晒干为末”,与糯米等和酒曲酿制。该书写作于明成化(1465-1487)年间,此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所谓“辣椒”应是辣之椒,椒指花椒,而非辣椒。以椒酿酒,早在《诗经·载芟》中已言之,以椒增香是极其古老的酿造传统,《齐民要术》即有胡椒、干姜和酒之法,不能仅因“辣椒”两字连称就以为必是辣椒。
笔者认为,我国文献最早的辣椒信息应是明王象晋《群芳谱》的记载:
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味甚辣。子种。王象晋《群芳谱》有称其为类书者,其实是分类撰述、纂辑之作,既有抄辑各类文献资料的成份,也多作者综述补录之言,用王象晋自叙所说是“取平日所涉历、咨询者类而著之”,其辑录也只是“以补咨询之所未备”。“番椒”条附录于“椒”目最后,未见前人言及,应是王象晋“咨询”所得。今所见明代《群芳谱》刻本王象晋自跋署天启元年(1621)。王象晋叙跋显示,《群芳谱》主要编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天启元年,时作者丁母忧继而被贬官居故乡新城(今山东桓台)。王象晋自叙称“历十余寒暑”,后来应有少量增补。崇祯二年(1629),王象晋起复,以参政督苏松常镇粮储,驻节江苏常熟。有学者考证,该书最初即由江苏常熟毛氏汲古阁刻印。
这是明朝著作中最早的番椒(辣椒)著录。内容极为简洁,包括别名、花色、果实的形状颜色口味以及种植方法等关键要素,除别名应属地方说法外,以今日科学知识衡量,其他无一不确。时间以定在王象晋自跋所署天启元年(1621)为是。当然这还有待弄清弦雪居本《遵生八笺》等类似内容的出现时间。
二、弦雪居本《遵生八笺》等同期江浙出版物时间偏后、说法混乱
接着必须弄清的问题是,《遵生八笺》弦雪居本的成书或初版时间是否会早于《群芳谱》?与《群芳谱》出版大致同时或稍后,苏杭一带还有一些农圃、花卉、生活百科类坊书也有“番椒”条目,一并考察。
(一)弦雪居本《遵生八笺》
关键是弦雪居本。此本清嘉庆以来广为翻刻,起源却不甚明了,弦雪居这一称号是书坊商号还是重订者的室斋雅称也不明确。明末清初陶珽所编《说郛续》已收有高濂《草花谱》,为弦雪居本《遵生八笺》草本内容的选辑本,其中也有“番椒”条。据此,弦雪居本《遵生八笺》应成书于《说郛续》出版前,即明末清初稍前。而弦雪居本又署明钟惺校阅,揣其情形,也属书商托名营销,应出版于天启五年(1625)钟惺去世后。今所见弦雪居本有两种: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永怀堂重订本,所谓重订应是针对雅尚斋本而言,馆藏著录为崇祯刻本,不明所据,但时间十分合理;二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课花书屋本,乃据永怀堂本重刻,时间应稍后。两种时间都晚于《群芳谱》,最早也只在明崇祯年间。
弦雪居本应出自江浙人士之手。重订翻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更是为了出版利益,对原书部分内容做了一些增删改易。其中卷3所加“临水观鱼”一条属苏州古吴茂苑之事,卷4杭州“飞来洞避暑”条加进不少文字,且更为详细,可见增订者应是吴下(苏州)或杭州一带人士。卷十二原“牛蒡菹”“牛蒡脯”换成高濂《野蔌谱》“江荞”“水菜”条,也都是苏杭一带水乡人士的偏好。而“番椒”一条,则应因《群芳谱》一书传入吴中,由吴人出版,就便据抄而补入。
比较弦雪居本与《群芳谱》的“番椒”内容,因是在原雅尚斋本“山茶花六种”条中删除文字换刻,只腾出两行空间,一行为标题,正文只得容纳在一行十八字内,不得不对《群芳谱》的“番椒”内容略作压缩和调整。弦本主要改动在删去“亦名秦椒”四字,替之以“丛生”二字。变化虽然简单,却特别值得注意。从下文所论山东地方志最初记载辣椒为“秦椒”可知,“亦名秦椒”应属鲁人所说,而非当时吴人所知,因而被直接删去。而所替“丛生”二字,则明显有错。辣椒是草本植物,无论在浙江还是山东都只是一年生,基部不丛生。究其原因,东晋郭璞《尔雅注》称“椒树丛生”,成了后世关于木本椒类植物的基本知识,弦雪居本增补者应是因椒之名添加“丛生”二字,竟不知与辣椒生长状况不合。这一删一添充分暴露了增补者对王象晋所说“番椒”基本无知,是抄录《群芳谱》而妄加改易。
(二)高濂《草芳谱》
該书或由弦雪居本相关内容拆版单印,也有可能相反,先有单行本,相应内容再集中融入弦本。其中“番椒”条,与弦雪居本完全一致。时间当与弦本同时或稍后。
(三)徐光启《农政全书》
徐光启(1562-1633),松江上海(今上海市)人。《农政全书》:“番椒,亦名秦椒,白花,子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味甚辣。”内容与《群芳谱》基本相同,也附于该书“椒”条最后。《农政全书》中徐光启自撰部分大约写作于万历末至天启初,与《群芳谱》同时。今所见《农政全书》则是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去世后由其门人陈子龙(1608-1647)等增订而成,崇祯十二年(1639)刊印。“番椒”内容恰恰属于增补部分,时间晚于《群芳谱》,应是抄录已传人吴中的《群芳谱》,目的只是列述不同椒种的性状,不及种植,因而删去“子种”二字。内容上最接近《群芳谱》,时间也应略早于包括弦雪居本在内的其他著作。
(四)《致富奇书》
该书编者署名陈继儒(1558-1639),或为假托。番椒条:“番椒,丛生,花似秃笔头,红如血,味辣,可充花椒用。”与弦雪居本大致相同。所加“丛生”二字,当由弦雪居本而来,也有可能两书是同一班作手。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句将“子”改为“花”,有两种可能:一是书贾刻书滥率马虎所致;二是因不了解辣椒的花、果形状,以传统椒类果实圆小推之,认为此处所说秃笔头、红如血,应是花的形状、颜色而妄改。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同时因属面向大众的经济实用指导书,又删去番椒“可观”之意,增加了“充花椒用”的功用说明。今所见该书最早的版本为清人重订本,序于康熙十七年(1678)。有论者称,此书已为明人戴羲《养余月令》引用,后者成书于崇祯六年(1633),十三年增补。就其内容和时间看,与弦雪居本、《草芳谱》应大致相同,由同时江浙书贾参照编合而成。
(五)《食物本草》
该书署名元李杲、明李时珍编著,卷首有天启元年(1621)钱允治序,崇祯十一年(1638)陈继儒序。书中又有崇祯十三、十四年间的内容,一般认为由明末姚可成编辑,刻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钱允治,苏州人;陈继儒,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姚可成,號蒿莱野人,生平不详,有称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该书个别版本有“吴门书林梓行”字样,应当出于苏州一带。其“番椒”条:“番椒,出蜀中,今处处有之,木本,低小,人植盆中,以作玩好。结实如铃,内子极细,研入食品,极辛辣。番椒,味辛温,无毒。主消宿食,解结气,开胃口,辟邪恶,杀腥气诸毒。”其中“结实如铃,内子极细”等描写比较切合辣椒的情况,但又冒出三个明显的疑点:第一,椒名既称“番椒”,又称“出蜀中”,两相矛盾。我国花椒有两大传统产地:一称蜀椒,来自巴蜀;一称秦椒,古称来自甘肃天水,一说来自秦岭。该书列述食物均标明产地,这里却舍弃《群芳谱》所说“秦”而改称“蜀”,应是因蜀椒比秦椒质优名盛择而言之,也有可能所说为蜀椒之别种,更有可能是编者因体例要求而随意添加,所说主治功效也与《本草纲目》“蜀椒”条下所说“散寒除湿,解郁结,消宿食”相近。第二,称番椒“木本”。我国传统花椒,后来西域、南洋传入之胡椒均为木本。辣椒中虽有木本一类,在热带或亚热带南部多年生也有一些木质化倾向,但在吴中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所说显然因椒之传统常识随意言之。第三,性状描写中强调了盆玩性质,所说“今处处有之”,也是明中叶李时珍《本草纲目》以来本草类著作描述“秦椒”常用的语言。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这段内容所说应主要依据用作盆景栽培的花椒、胡椒类植物知识,融合了一些“番椒”即辣椒的耳闻信息而成。
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徐光启《农政全书》是正规农书,基本严守《群芳谱》的内容,其他两种,则与弦雪居本《遵生八笺》情况基本相同。后三者“番椒”内容有这样几点共性:第一,对辣椒性状的描述多少都有改窜,而改动的部分既有少量关于辣椒性状更为具体化的成分,也包含了一些与辣椒完全无关或明显不合的内容。第二,编写者多强调观赏价值,显然混杂了一些灌木、藤本椒类盆栽植物的观赏印象和栽培经验。在具体的描述中也就出现了丛生、木本、产于蜀中等完全脱离辣椒实际,更多指向花椒、胡椒类植物性状的内容。第三,辣椒的名称有了明显的变化,统一放弃了“亦名秦椒”之说,与《群芳谱》有了明显的距离。时间稍晚的《食物本草》称“出蜀中”,与《群芳谱》所说“番椒”更是完全不同。这些异常的信息都可见编者对《群芳谱》所说番椒了解极为有限或基本无知,多应是因《群芳谱》所载名目及内容,牵附相应的文人盆玩清供经验和传统椒类知识编述凑数而已,所说植物实际与木本花椒、胡椒类植物更为贴近,或许多少也融合了一些番椒(辣椒)的耳闻信息。
这种情景还可进一步联系清陈溴《花镜》中的相应内容来把握:“番椒,一名海疯藤,俗名辣茄。本高一二尺,丛生,白花。秋深结子,俨如秃笔头,倒垂,初绿,后朱红,悬挂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冬月取以代胡椒。收子待来春再种。”陈溴(1615-1703),一作陈溴子,杭州人,与上述诸书属于同一地域。自序署康熙二十七年(1688),时间较前几种又过去了三四十年,有关记载值得更多期待。所说也确实远为详细,而且出现了“辣茄”这一新的名称,显然所指是辣椒。但存在的问题却同样明显。所谓“丛生”、形如“秃笔头”“悬挂可观”、味辣“代胡椒”都明显沿袭弦雪居本《遵生八笺》和《致富全书》所说。同样也删去“秦椒”别名,又特地冒出另一别名“海疯藤”,并称“秋深结子”,则是更严重的破绽。所谓海疯藤,也作海风藤,前人本草、医书已多次提及,今称为胡椒科植物,木质藤本,与辣椒并非一物。明朝著述中,有一种海疯藤的资料与《花镜》所说适可参照。王路《花史左编》:“地珊瑚:产凤阳诸郡中,其子红亮,克肖珊瑚,状若笔尖下悬。不畏霜雪,初青后红。子可种,又名海疯藤。子有毒,甚辣,不可入口。”作者王路是槜李(今浙江嘉兴)人,这段记载也几乎全文见于《遵生八笺》,与“番椒”同卷,归于观果花卉之类。陈淏所说虽然名称已十分明确,但明显混杂了这种地珊瑚(海疯藤)的相关知识,与明末清初书坊编者一样,仍是抟合木本椒类植物与耳闻辣椒信息而成。
上述明末清初江浙一带书坊编书和文人著作,尤其是弦雪居本《遵生八笺》,通常被人们视作江浙一带辣椒领先传播的信息或证据,但这些著作大都出于明末清初,时间晚于《群芳谱》。除《农政全书》全然抄辑《群芳谱》外,其他有改动者多是掺合花椒、胡椒类木本植物相关知识和盆景制作经验而成。从下文的论述可知,入清后浙江以及江苏苏南地区早期方志物产志中的辣椒记载未见使用番椒、秦椒名称,与这些明末清初坊书“番椒”内容也了无瓜葛。显然,这些坊书的“番椒”内容没有多少苏杭当地的生活依据,应是坊间文人就《群芳谱》的番椒内容抄辑编列,随意改动,是非错杂,不可据信。其中或多或少有些辣椒的影子,也远不明确,整体看与花椒、胡椒近,与辣椒远,远不如王象晋《群芳谱》所说明确纯粹、切实准确。因此,无论从写作时间还是实际内容看,都以《群芳谱》的“番椒”内容更原始、更切实,是我国辣椒时间最早,也最为真切可靠的记载,而同期江浙人士对辣椒应是所知甚少或基本无知。
三、秦椒:辣椒在山东的起源与北方的传播
在明确最早记载辣椒的文献和时间后,进一步就是对后续传播过程的追踪梳理。清道光以来,我国方志辣椒记载较为普遍,各地辣椒食用习性基本定型,尤其是道光年间吴其溶《植物名實图考》概括当时情景,“辣椒处处有之,江西、湖南、黔、蜀种以为蔬”,更是标志着我国传统辣椒分布和食用核心局面的形成。笔者的考察和讨论集中在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我国辣椒初传和不断兴起的过程,这可谓我国辣椒传播的早期阶段。综合各方面的文献信息,我国辣椒的早期传播分为三大版块或三大区系,每一版块或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源头或起点,也有大致统一的名称体系、分布特征。三大版块起步有先后,发展有快慢,相互间也有一些交接影响与交叉渗透。透过这一逐步展开的时空结构,可以切实、简洁地把握我国辣椒起源与早期传播的基本途径、发展进程和分布格局,深入了解晚清以来我国辣椒种植生产、食用风气区域差异的历史渊源。
首先讨论第一版块即辣椒在我国北方地区的起源与传播情况。这一区系大致南以淮河(东端则是长江)、秦岭为界,即通常人们所说北方地区,包括山东、河南以及今“三北”地区核心部分的广大范围。我国辣椒最早发源于这一线的东部沿海,向北、向西渐次传播,展现出比较连续的过程和相对统一的特点。
(一)我国辣椒起源于山东
笔者认定王象晋《群芳谱》所载“番椒”是我国最早的辣椒信息,山东地方志恰好有相应的佐证。王象晋是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我国方志最早的辣椒记载也出现在山东,时间同在明末。胡义尹《明清民国时期辣椒在中国的引种传播研究》是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有一节专门论述“明代辣椒的引种”,举嘉靖河北《南宫县志》“辣角”、福建《清流县志》“红椒”、崇祯山东《历城县志》“秦椒”为明代方志最可能的辣椒信息,并基本推翻前两种,认为《历城县志》所说秦椒“当是辣椒”。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崇祯十三年(1640)《历城县志》所载秦椒应即《群芳谱》所说番椒别名,是当地土俗称呼,其他两种都明确另有所指,绝不可能是辣椒。该志在药类中记载“花椒”,在蔬类与马齿苋、地瓜一起记载“秦椒”,视为“野蔬”。后来《(乾隆)历城县志》在药类中著录“秦椒,生泰山川谷,八月九月采实”,这是花椒,而在蔬类中记载“秦椒”,则移为家蔬,与“刀豆、苜蓿、香芋”同类,是为辣椒,原来与“秦椒”并列的马齿苋仍保留在野蔬中,反映了当地辣椒由野生到种植的演化过程。当然,从《群芳谱》所说番椒“子种”可见,王象晋掌握的信息已是应用栽培,所说应是其故乡新城一带的情况。历城在济南附近,新城更近大海,番椒(秦椒)的出现更早。而最初以椒命名,应即着眼食用。
人清后,康熙十二年(1673)《齐河县志》(卷3)、乾隆元年(1736)《(雍正)山东通志》(卷24)、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青城县志》(卷1)、《(乾隆)沂州府志》(卷11)相继记载秦椒,而且都属蔬菜性质。《(雍正)山东通志》《(乾隆)沂州府志》进一步指明“秦椒,色红,有子,与花椒味俱辛”,是明确的辣椒无疑。齐河今属德州,与济南相邻。青城今并入高青县,是王象晋故乡新城的北邻。沂州即今临沂市。这些都说明,从王象晋写作《群芳谱》的天启元年(1621)到清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间,在今山东核心地区,主要是桓城、济南一带,俗名秦椒的辣椒已逐步形成分布规模,山东可以说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并有持续发展迹象的辣椒分布区。正是由于文人著作与方志记载两方面的相互印证,笔者确认山东是我国辣椒的历史起点,我国辣椒发源于山东。
(二)秦椒是北方地区对辣椒的通称
王象晋记载“番椒,亦名秦椒”,番椒应是一个书面雅称,反映了王象晋这类文人对辣椒为外来物种这一性质的判断,而秦椒则应是山东民间俗称,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说法。这一名称不仅流行于山东,在华北、西北乃至东北地区都较通行。这个被明末清初江浙坊书弃而不用的名称,在康熙年间(1662-1722)的北方地区几乎成为一个通名,各地最早的方志记载基本使用这一名称。浙江高士奇(1645-1703)为康熙宠臣,长期在京城任职,晚年退居杭州,康熙二十九年(1690)著《北墅抱瓮录》,记录辣椒:“秦椒,枝叶尽绿,高一二尺,开白花。结子长二寸许,深秋色红,磊磊可喜,味之辛烈,过于姜桂。”不用浙人所说“辣茄”或王象晋所说“番椒”,而只称“秦椒”,正是长期京城生活习得的知识。康熙四十七年(1708)汪灏等人奉旨编成《广群芳谱》,在原《群芳谱》“秦椒”条下以小字注称:“以产自秦地故名,今北方秦椒另有一种。”后一句王象晋《群芳谱》本无,是《广群芳谱》编者新加,说的是康熙年间北方的情况。所谓另一种秦椒即指王象晋所说番椒,在北方地区已成通名。此后北方广大地区的方志长期坚持使用,《广群芳谱》这一句也为后世许多方志记载“秦椒”时所引用,受其影响后世不少方志以秦椒为别称乃至正名。
“秦椒”这一辣椒名称流行的范围在东部以长江、淮河为界,江苏省地跨长江南北,江北的《(雍正)安东县志》(今江苏涟水县)、《(乾隆)淮安府志》称秦椒。江南(含今上海市)的《(嘉庆)直隶太仓卅I志》《(道光)昆新两县志》《(道光)川沙抚民厅志》称辣椒和辣茄。在西部则以秦岭为界,秦岭南坡今陕西所属地区兼用他名,而秦岭以北广大地区多只称秦椒。因此,可以说秦椒是一个主要在北方地区长期流行的辣椒通名。
(三)秦椒由山东向北、向西逐步传播
在整个北方地区,辣椒的名称基本一致,这表明相互间种植和食用风气有着紧密联系。事实上,从地方志的记载看,也确是以山东为起点,称作秦椒的辣椒在淮河、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东向北、向西渐次传播。康熙十一年(1672)河北阜城(《重修阜志》卷1)、康熙十六年(1677)辽宁铁岭(《铁岭县志》卷4)、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蓟县(《蓟州志》)、康熙六十一年(1722)北京顺义(《顺义县志》卷2)、乾隆二年(1737)甘肃酒泉(《重修肃州新志》物产)、乾隆十年(1745)河南洛阳(《洛阳县志》卷1)、嘉庆十五年(1810)黑龙江(《黑龙江外记》卷8)均以秦椒之名为各省区方志辣椒记载之始。河南的秦椒信息尚有更早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景日畛《说嵩》:“秦椒,非椒也,味极辣,农人多食之。”在北方时间仅晚于山东、河北(含今京津)、辽宁。陕西的情况特殊些,最早的记载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山阳县初志》(卷3),因在秦岭南坡,称“番椒”,而《(雍正)陕西通志》“俗呼番椒为秦椒”(卷43),还有乾隆十八年(1753)《宜川县志》所说“秦椒,俗名辣子”(卷3),反映的都是秦岭以北的情景。乾隆十九年(1754)《白水县志》则又称辣椒,是北方地区的一个特例。
从时间上看,秦椒有明显自东向北、向西渐次传播的趋势。其中与京、津、冀同属华北的山西出现时间稍晚,乾隆三十五年(1770)《孝义县志》始有同类秦椒与花椒并列见载,称“邑人多业圃……诸菜中白菜、罗卜,尤多秦椒”,可見传种有年,已成盛势。康熙四十九年(1710)山西西北部保德县志记载的“辣角子”有可能是辣椒,这一名称在晋、陕、甘都有少量地方使用。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山西境内的辣椒出现就不太晚,而由山东至西北陕西、甘肃逐步传播的过程也就更加自然、顺畅。
(四)鲁冀京津辽是我国最早的辣椒盛传与嗜食区
在上述北方地区,河北(含今京津)、辽宁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河北最早记载秦椒(辣椒)的阜城与山东德州毗邻,时间上也仅稍晚于山东。此后康熙年间天津蓟县(《蓟州志》卷3)、北京顺义(《顺义县志》卷2),雍正年间(1723-1735)河北保定顺平(《直隶完县志》卷4)、北京市(雍正《畿辅通志》卷56),乾隆间(1736-1795)河北沧州献县(《献县志》物产)、沧州市(《沧州志》卷4)、衡水饶阳(《饶阳县志》卷上)、唐山丰润(《丰润县志》卷4)、保定安国(《祁州志》卷7)、石家庄市(《正定府志》卷12)、沧州任丘(《任邱县志》卷3)、石家庄辛集(《束鹿县志》卷10)、邢台隆尧(《隆平县志》卷3)、邯郸鸡泽(《鸡泽县志》卷8)、石家庄高邑(《新修高邑县志》卷1)、廊坊永清(《永清县志》户书)等地相继记载秦椒,涵盖整个河北中南部与京津所属地区。
在辽宁,蒋慕东、王思明先生已经注意到方志记载“早而且多”,认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辽人林本裕《辽载前集》为最早:
秦椒一名番椒,形如马乳,色似珊瑚,非本草秦地之花椒,即中土辣茄也。其实还有更早的,康熙十六年(1677)铁岭(《铁岭县志》卷下)、康熙二十一年(1682)营口盖州(《盖平县志》卷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辽宁通志(《盛京通志》卷21)都在蔬类中记载秦椒,《(康熙)盛京通志》明确称“土产只有此种”。后来《(咸丰)盛京通志》在讲明花椒“此地寒,种之者少”后,对秦椒有详细的描述:“秦椒,结椒长于枣,而上锐,生青熟红,味极辛,土人多食之。”辽地所说秦椒正与山东、河北、京津地区一样指辣椒。《辽载前集》与同一时期高士奇《北墅抱瓮录》都是继《群芳谱》之后关于秦椒较为明确、具体的记载,注意《辽载前集》所说番椒、秦椒两种名称的关系与王象晋正好相反,高士奇也只称秦椒而不出别名,都进一步表明秦椒之名盛行于北方地区。
地方志信息充分显示,从山东到河北、京津地区再到辽宁的环渤海地区,以华北平原为核心,山东、辽宁为两翼,在康乾时期已经形成一个辣椒的密集分布区,记载时间早,分布密度大。其他方面的信息也有佐证,清初广东屈大均《闭瓮菜》诗:“北人重御冬,菜茹多旨蓄……北人喜芳辣,姜桂日餐服。牲用煎茱萸,濡鱼多实蓼。贵以辟天寒,口体非相逐。”这是康熙前期,是说北人平日喜食辛香之物,冬天比较寒冷,因而尤重蓄制腌菜之类,所用是姜、桂、茱萸、辣蓼等传统辛辣调味之品。而苏州郭麐《樗园销夏录》:
辣椒,吴人谓之辣虎,又谓辣茄,亦止用为酱,仅食少许耳。而北人堆盘生食,以
盐蘸之,可尽数枚,信乎口之于味不同嗜也!这是乾隆(1736-1795)末年,郭氏居江苏扬州,所说北人当主要指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山东、河北、京津地区,当然也可包括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地,而所嗜辣品已重辣椒一种。众所周知,嘉庆、道光以来湘赣川黔民风嗜辣,而在清之早期,至少在康乾时期,此风却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为盛。此间京、津、冀、鲁、辽诸地方志记载辣椒之多,正是这种风气的反映。此后,晋、陕、甘、吉、黑等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逐步受到感染传带,对辣椒的记载与喜好也略胜于江、浙、闽等华东诸省。
四、番椒、辣茄、番姜:华东地区辣椒的稀散分布
这里所说的华东地区,排除了属于北方的山东,只及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和内陆的安徽、江西。这是紧继山东之后,方志记载出现较早却相对稀少、分散的地区,有着大致统一的区域特征。
(一)江苏、浙江方志记载早而少
这一大区中,江浙两省方志的辣椒信息出现较早。与崇祯十三年(1640)山东《历城县志》同年,江苏长江边《(崇祯)江阴县志》“土产”中也记载了番椒:“草有书带芭蕉,鸡冠虎耳,薜荔番椒,间亦作花。”所说番椒,明确归为草类,与同一时期苏杭一带《草花谱》《致富奇书》中多称木本不同。遗憾的是,后续《江阴县志》及邻近方志都没有任何对应信息,是否与《群芳谱》所载相同,无法确定。
这一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辣椒以浙江为发轫,方志明确可靠的记载最早见于康熙十年(1671)浙东绍兴《山阴县志》:“辣茄:红色,状如菱,可以代椒。”这一名称及相应的描述与《群芳谱》所说“番椒”明显不同,与前述明末清初江浙一带书坊编著相应内容也完全绝缘。辣茄是康熙以来吴越即今苏南至浙东比较通行的名称,后来这些地方的方志也多沿用这一称呼,渐为外方人士认同。不仅是辣茄,康熙二十六年(1687)《仁和县志》第一次称辣椒,这一名称或者兼取浙东辣茄和北方秦椒而成。两个相对科学、后世成为通称的辣椒名称都首先出现在钱塘江出海口的南北两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可能这里的辣椒最初与山东所谓秦椒、番椒联系无多,是相对独立的源头,有着不同的海外来源。
江苏(含上海)介于浙江与山东之间,地跨长江南北,辣椒的传播明显受到南北两路的不同作用。可靠的最早记载是雍正五年(1727)《安东县志》(卷6,今江苏涟水),然后是乾隆十三年《淮安府志》(卷24),都在江北、大运河沿线,所载名称都是“秦椒”,显然这里的辣椒应来自山东。而江苏的江南地区,记载时间远晚于江北,更晚于浙江。相继有《(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7)、《(道光)昆新两县志》(卷8)、《(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卷11),使用的名称是辣茄或辣椒,与绍兴、杭州地区完全一致,这里的辣椒应来自浙江。
尽管两省尤其是浙江方志记载出现较早,但人们的实际了解十分有限。康熙二十五年(1686)《杭州府志》记载仍称辣茄为“盆几之玩”“不可食”,主要用作观赏,同时杭州陈溴《花镜》相关说法更是模糊不清,不能不说除高士奇那样长期仕北者之外,吴越人士对辣椒实际了解不多,生活应用更是寥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江浙两省方志的辣椒记载数量较少,虽然方志未载不能即认其无传,但也大致表明这一带的种植食用较为淡薄。
(二)番姜:台湾、福建的特殊情况
福建与台湾的辣椒信息联系紧密,有必要合并介绍。就方志记载而言,台湾还稍早些。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台湾府志》引用清人六十七《台湾采风图考》的记载:
番姜,木本,种自荷兰。开花白瓣,绿实尖长,熟时朱红夺目,中有子辛辣。番人
带壳啖之。内地名番椒。更有一种结实圆而微尖,似柰种,出咬巴(引者按:印尼雅加
达),内地所无也。清人六十七(居鲁)乾隆九年(1744)人台采方问俗,于乾隆十年著成《台湾采风图考》。后来台湾地方志记载辣椒多抄录这段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称辣椒为番姜,椒、姜音近,也可能是味比生姜而附名,或出当地土语记音。称为木本,应是气候炎热多年生长而显现木质化倾向,也有可能所说域外所传木本品种。这一记载是我国古代文献有关辣椒来源最具体明确的信息,可见与内地所见品种完全不同,有着台湾地区品种及生长状态的特殊性。
福建最早的记载见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安溪县志》药类:“番椒,一名番姜,一名秦椒。花细白,实老红,味辣,能解水族毒。食鱼蟹过多者或泄泻或胀满,用子煎汤服。”安溪今属泉州,离海不远,显然主要作为药用。记载的名称也很有代表性,番椒、秦椒出于《群芳谱》,到乾隆年间已成通识,而番姜之称又显然来自台湾,表明这里的辣椒来源或为多元,既有来自台湾的,也有可能是内地已有的。此后乾隆年间泉州《泉州府志》(卷19)、《晋江县志》(卷1),厦门附近《马巷厅志》(卷12)都有类似记载,用途也都在治疗食鱼之毒。而在其他地区,如《(乾隆)建宁县志》(卷6)、《(道光)永安县续志》(卷9)则记载正名秦椒外,称俗名茄椒、胡椒鼻之类,两县都在福建内陆今三明市中西部,显然与沿海地区不同,可能多少受到相邻内地的影响。
(三)安徽、江西的零散记载
安徽、江西在华东地区不属沿海,安徽地跨长江南北,江西在江南更為内陆,辣椒记载时间较沿海明显偏后,数量偏少,也更加分散。所用名称番椒、辣椒、茄椒兼而有之,带着辣椒广泛流传后的迹象。安徽最早的记载称为辣茄,见于乾隆十七年(1752)的《颍州府志》及稍后属下阜阳《(乾隆)阜阳县志》(卷5),都在今淮北阜阳市。江南今芜湖属下南陵(《(嘉庆)南陵县志》卷5)、繁昌(《(道光)繁昌县志》卷6)时间偏后,已称辣椒,安徽辣椒应主要来自江浙。江西方志记载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会昌县志》:
番椒(有二种,嫩时色碧绿,老则朱红,形如猪牙。稍圆而嘴尖者名鸡心椒,辛辣
可辟瘴)、花椒、茱萸。时间虽然不算早,但品种却具体多样,来源或闽或粤,值得注意,隐有后来赣南嗜辣风气的某些苗头。其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建昌府志》(卷9)、乾隆二十五年《袁州府志》(卷7)、道光三年(1823)《信丰县志续编》(卷4)、道光五年《宜黄县志》(卷12)、《丰城县志》(卷1)等也有记载。
综观上述华东诸地包括台湾,由于大都地处沿海,辣椒起步并不迟。名称始则辣茄,继则辣椒,内地后出记载也使用番椒一类通称,另有明确来自域外的“番姜”,乾隆以来更有一些不同品种的记载,表明源头应与山东有所不同,有更多东南海路直接传来的可能。方志记载比较零散,表明这一线辣椒种植和食用风气与山东、华北相比较为薄弱。
(四)江西少数地区嗜辣成风
江西的情况有些特殊,方志记载虽少,而鄱阳人章穆《调疾饮食辩》对辣椒却有这样一段评述:
辣枚子:近数十年,群嗜一物,名辣枚,又名辣椒,亦蔊菜之类也。叶如蘑卜而薄,枝干高尺余,四五月开小白花。结子前后相续,初青后赤。味辛辣如火,食之令人唇舌作肿。而嗜者众,或盐腌,或生食,或拌盐豉炸食,不少间断。至秋时最后生者.色青不赤,日干碾粉,犹作酱食。其形状不一,有本大末小者,有本小末大者;有大如拇指,长一、二寸者.有小如筋头,短仅一、二分者;有四棱如柿实形者,有圆如红琅玕、火
齐珠者。植盆中为玩可也,今食者十之七八,而痔疮、便血、吐血,及小儿痘殇亦多十
之七八(父母嗜食辛辣,其精血必热,故遗害于儿女)。作者生平不详,此书自序于嘉庆十八年(1813),作于晚年,属食物本草类著作,分类编述食物性味、功用、宜忌,间有名实考辨,所言多较切实。这是道光年间(1821-1850)吴其溶《植物名实图考》前最为具体、详细的辣椒资料。所指地区不明,所说“辣枚”之名他处并江西方志都未见,所说嗜食情景应以其乡邑即今江西鄱阳一带为主。称当地嗜食辣椒已有数十年,正是乾隆(1736-1795)中叶以来的情况,可见至少江西少数地区种植、食用辣椒的风气已十分兴盛,而且所说各类品种与前引赣南《(乾隆)会昌县志》的品种信息相呼应,可见江西辣椒的品种较为丰富,应是种植兴盛有日。吴其溶《植物名实图考》所说“江西、湖南、黔、蜀种以为蔬”,江西位列第一,今人苦于同一时期江西方志记载极少,而章氏所说适可印证。后世将江西与湖南、贵州、重庆、四川同归我国嗜辣区,至迟乾隆中叶应有一些地区即已开始,这是需要特别指明的。
五、番椒、海椒、辣子:辣椒在中南、西南地区的特殊起源与火辣盛传
这里所说的两大地区要排除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河南的情况归属整个北方大区的传播过程中,剩下的为华南的广东、广西,华中的湖南、湖北,西南的贵州、云南、重庆、四川诸省区。这是第三个传播关系比较紧密的版块或区系,时间紧接华东之后,覆盖面积较大,以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为中心,兼收南北来源,深得社会助力,辣椒得以大肆传播,构成了我国辣椒传播史的盛大景观。
(一)广东辣椒起于南海之滨
在上述三区中,广东的情况有必要首先一提。广东方志的辣椒记载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阳江,《(康熙)阳春县志》:“番椒,枝茎柔弱,高可一二尺,结角深红色,中有子,如麻大,其角最为辛辣。”时间晚于浙江,但记载十分明确,说清了辣椒生长的基本性状,显然应是种植有日或传自相关知识较为明确的地区。此后乾隆年间梅州丰顺(《丰顺县志》卷7)、江门恩平(《恩平县志》卷9)、惠州惠阳(《归善县志》卷16,归善县今分属惠州惠阳、惠城等地)、道光年间江门开平(《开平县志》卷4)相继记载辣椒。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诸地所说名称或番椒或辣椒、辣茄,也偶见别名秦椒,与南方记载辣椒较早的东部沿海浙江、福建比较接近;二是所载诸地几乎都在沿海,离海最远如丰顺,也只是由汕头、揭阳上溯榕江即至,而同期内陆粤中、粤北未见记载。因此,笔者认为,广东的辣椒应来自海上,主要似由浙江、福建一线经海路辗转而来,当然不能排除由海外直接传人的可能,而且乾隆(1736-1795)以来这种可能性更大。
(二)湖南辣椒名称特殊、时间超前,最初应来自广东沿海
湖南在内地,而方志记载辣椒之早之密令人称奇。康熙二十三年(1684),今邵阳市所辖《宝庆府志》《邵阳县志》府县两级方志同时在“蔬之属”中记载“海椒”(分别见卷13、卷6),根据后世方志对应的说明,所谓海椒即辣椒,这一时间较广东还稍早。更早的康熙二年(1663)宝庆府所属《武冈州志》物产志在“蔬之属”中列“萝葡菜、白菜、茄、椒”,这里单字“椒”与后来的海椒即辣椒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乾隆以来在湘西一线,先后有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泸溪(《泸溪县志》卷7)、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花垣(段汝霖《楚南苗志》卷1,该志就整个湘西苗乡而言)、怀化溆浦(《溆浦县志》卷7)、怀化市北部清辰州府(治所驻今怀化沅陵,《辰州府志》卷15),嘉庆年间怀化市通道(《通道县志》风土志)、张家界慈利(《重修慈利县志》卷2)、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龙山县志》卷8)、张家界市(《永定县志》物产志),道光年间怀化辰溪(《辰溪县志》卷37)、邵阳新宁(《重辑新宁县志》卷30)、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凤凰厅志》卷18)相继记载辣椒。这里都是湘西山区和沅水、资水上游河谷丘陵山区。所说名称主要是海椒,也有少量称番椒和秦椒。地缘关系十分紧密,分布较为密集,俨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辣椒种植、食用分布区。
同时主要称海椒的还有永州一带。道光八年(1828)《永州府志》引佚名《湘侨闻见偶记》:
西南之民秉气中寒,嗜椒成性,然在昔仅有秦、蜀诸椒耳,近乃盛行番椒,永州谓之海椒。其叶似竹而有棱无刺,其花白,其实角,圆者若果,长者若小豆荚。初深碧,渐老色红。子在角中,色白。土人每取青者连皮生啖之,味辣甚诸椒,亦称辣子。性散气动火,人以其爽口,多偏嗜,往往受损。永州作齑菜,必与此同淹,寻常作饮馔,无不用者。故其人多目疾血疾。……番椒之入中国盖未久也,由西南而东北,习染所
移,与淡巴菰(引者按:烟草)等,是亦可谓妖物也与!大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作者寓居永州,写下此记,所叙情景正与前引江西章穆所说相似。所谓辣椒由西南而东北,应是有感于当时湘西、贵州乃至云南、广西等地辣椒食用兴盛而有此印象。提到永州当地称番椒为海椒,与湘西相同,而永州比邵阳、怀化更近广东。
在湖南东部,乾隆年间永州祁阳(《祁阳县志》卷4)、郴州资兴(《兴宁县志》卷4)、岳阳湘阴(《湘阴县志》卷11),嘉庆年间长沙(《长沙县志》风土)等都记载辣椒,只是名称与湘西明显不同,南部多用广东一线常说的番椒,北部长沙、湘阴等地应是受到北方影响多称秦椒。
有一个问题无疑令人至为关注,即湘西邵阳、怀化至张家界一线深处内陆山区,称作海椒,“俗名辣子”的辣椒,出现时间比周边都要早,这里的辣椒到底来自哪里?已有的讨论分为两派:一派因视浙人最早记载辣椒,认为湖南的辣椒应由浙江一带沿长江西上,经洞庭、沅湘南传;另一派认为就近来自广东。笔者认为,湘西与浙江相去较远。从方志记载看,辣椒在湖湘与江浙之间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三地记载都偏迟,远晚于湖南,分布也比较分散稀少。即使在湖南内部,方志记载也是东部晚于、少于西部,北部晚于、少于南部,湖南的辣椒最初经长江水路先西上再南进传人湘西的可能性不大。
而来自广东的说法,尽管有关论证比较粗疏,但可能性更大些。这里主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湖南与两广接壤,湖南的辣椒先南后北,源头应在南方,而从广东传入距离较近。第二,湘西、湘南最初称辣椒为海椒,广东辣椒的最早记载虽然时间稍晚两三年,但恰好高度集中于沿海。在两地记载大致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这种情景起人联想,其中或有民间偶然性人口流动如商贩活动、文人游宦等由广东沿海传带湖南的可能。第三,已有學者注意到,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是说广州附近一些人口繁庶之县多往江西、两湖一线贩卖番椒。所说番椒是否指辣椒颇费思量,《广东新语》物语有专门的“椒”业一条,主要说的是胡椒、花椒之类,并未提到“番椒”,屈氏其他著作也没有再次出现番椒这一概念,所说番椒应指胡椒,至少很难认定其必指辣椒。不过《广东新语》出版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广东方志也正是该年开始记载番椒,屈大均著述并不苟且,有可能所说至少包括辣椒。既然已经远途贩运,也就有一定种植历史和规模,就近北传湖南也较为自然。第四,湖北《(乾隆)归州志》(治所驻今秭归)土产蔬属中记载“广椒”,所指即辣椒。《(道光)鹤峰州志》(今属湖北恩施)更是明确记载:“番椒,俗呼海椒,一呼辣椒,一呼广椒。”这些记载都明确归入蔬类,与海椒、番椒为一物,所指是辣椒无疑。鹤峰、归州与湘西北部同属武陵山脉,民风相通,尤其是鹤峰与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紧邻,所说海椒、广椒同为辣椒俗名,应多少反映了当地所谓海椒的实际来源。第五,广东最早记载的《(康熙)阳春县志》称辣椒“结角”,湖南最早描述辣椒形状的《(乾隆)辰州府志》称“状如新月”,果形大致对应。正是基于这几点考虑,笔者认为湘西邵阳、怀化一线最初的辣椒应来自广东沿海,因而多称海椒。也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笔者将广东作为起点,与广西一起纳入以湖南、贵州、重庆、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传播大区中。
(三)贵州、云南、广西的跟进传播
以湘西南部为中心,辣椒首先在南部向贵州、广西、云南传播。贵州方志的最早记载应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余庆县志》:
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康熙六十一年(1722)《思州府志》也有相应的记载。乾隆六年(1741)《贵州通志》则完全抄录《余庆县志》的内容。余庆县在今遵义市最东南,与铜仁市相邻。思州府治所在今铜仁市思南县,与湖南怀化相去不太远,这里的辣椒应与这一带南瓜的来源一样,由湘西传人。贵州的辣椒名称,除海椒外,还通行辣子、辣角、辣火等俗名,都与湘西比较一致,两地渊源关系极深。
广西与湘西、贵州一样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最早的辣椒记载见于乾隆元年(1736)《(雍正)广西通志》:“兴隆土司猛苗杂居,锄畲种粟。每岁正月,男女聚墟市,联歌欢洽,各以槟榔致赠。疾病巫祷,罄产勿惜。每食烂饭,辣椒作盐。”兴隆土司在今南宁市所属马山县一带,乾隆年间庆远府(《庆远府志》卷3,今广西河池市一带)、柳州府(《柳州府志》卷12)、梧州府所属州县(《马坪县志》卷2、《梧州府志》卷2)也有记载。与广东的情况不同,广西方志中的辣椒记载并不始于沿海或南部,也不以毗邻广东的地区为先,而是相对集中于偏北、更靠近贵州的地方,因此辣椒的传播更有可能来自于北边的湖南、贵州,而非东南沿海。广西方志的记载多直称辣椒,也与湘西、贵州一带所说辣子、辣角更为接近。
云南的辣椒记载首见于乾隆元年(1736)《(雍正)云南通志》:“秦椒,俗名辣子。”同时广西通志却没有类似的内容,可见云南的辣椒应不比广西迟。乾隆年间昆明(《广西府志》卷20,治所驻今云南泸西)、楚雄(《白盐井志》卷3)、昭通(《镇雄州志》卷5)、保山(《永昌府志》卷23)、思茅(《景东直隶厅志》卷4)一线也有记载,地点多集中在中北部。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方志记载的名称多沿用通志所说,采取“双轨制”,秦椒是北方流行的俗名,在这里成了雅称,应与最初通志修志官员多来自北方有关,而辣子则是俗名,应来自相邻的贵州等地。
贵州、云南、广西三地辣椒的传播统一于以湘西为中心的发散区,尤其是贵州紧随湘西之后,分布较多,势头较为强劲,连带东西相邻的广西、云南,形成引种和食用辣椒的连片区域。这种整体趋势除紧密的地缘关系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两种社会因素:第一,贵州等地食盐资源严重缺乏,加之高原山区运输困难,盐价奇高,有寻求相对廉价方便替代品的需求。康熙二十九年(1690)田雯《黔书》就提到黔地“当其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狗椒非辣椒,是一种野生花椒类植物,民间就近取材,早用在先,而辣椒之辣远过于狗椒,更适应人们的需求,因而一旦出现,便广受欢迎,迅速传开。尤其是底层民众,由于贫穷,缺盐尤甚,种植食用辣椒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在广西等不太缺盐之地,辣椒则又有“消水气,解瘴毒”的作用,也受到特别欢迎。第二,苗、瑶等少数民族的突出作用。《(康熙)余庆县志》《(雍正)广西通志》《(乾隆)贵州通志》都提到苗民以辣椒代盐。湘西山区本就是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境内辣椒分布密集区,两者的基本叠合正反映了少数民族在辣椒食用上的共同爱好。苗、瑶等少数民族内部生活风习的紧密联系和在西南山区的迁移发展,有力促进了辣椒在贵州、广西、云南三地的传播。正是由于这些地理状况、环境资源、民族分布等社会、自然条件的相互作用,促进了辣椒从湘西向贵州、广西、云南的迅猛传播以及乾隆以来以湘西、贵州为中心的辣椒嗜食风气迅速形成并不断发展。
(四)秦椒与海椒:南北两路在湖北、重庆、四川的交集渗透与终极汇流
湖北、重庆、四川三省区居于我国中部核心地区,远离沿海源头,同时又都地跨长江南北,在辣椒自东向西传播过程中,有着南北两路在此交集汇流的迹象。但由于整体上受湖南、贵州等地影响更大些,最终形成的嗜辣风气也与湖南、贵州等核心区完全连成一片,因而与之合为统一的大区。
湖北全省山水错综支离,西部为长江、汉水两岸连绵大山,植被丰茂,是我国传统椒类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湖北辣椒记载出现较迟,相关信息较为分散,也较模糊。乾隆十九年(1754)《长阳县志》是最早的记载:“山胡椒、辣子(有二种)。”长阳今属宜昌市,在长江南岸,所谓辣子无论名称还是来源都应与湘西密切相关。此后《(乾隆)归州志》称广椒,《(嘉庆)郧阳志》称秦椒,《(道光)鹤峰州志》则一并记载:“番椒,俗呼海椒,一呼辣椒,一呼广椒。”来源显然有南北两路,称秦椒如今属十堰市的郧阳源于北方系统,海椒、辣子、广椒则明显源于南方,有南北两路夹进、交相渗透的色彩,而以南来为主。
四川与重庆今分治不久,无论地理还是政区传统上一直作为一个整体,方志记载早于湖北。重庆最早见于乾隆二年(1737)《璧山县志》,在蔬菜中记载秦椒。璧山紧邻重庆,巴蜀多川椒,所說秦椒应指辣椒。四川最早见于乾隆十四年(1749)《大邑县志》:“秦椒,又名海椒。”两志记载的秦椒与海椒,从名称上说,在整个四川盆地有一定的代表性、象征性。乾隆前期,今眉山市彭山(《彭山县志》卷1)、丹棱(《丹棱县志》卷5)、青神(《青神县志》卷5)、宜宾市珙县(《珙县志》卷4)相继记载秦椒。嘉庆年间,今成都市金堂(《金堂县志》卷3)、德阳市广汉(《汉州志》卷39)、眉山市洪雅(《洪雅县志》卷4)、成都(《成都县志》卷6),道光年间资阳市安岳(《安岳县志》卷15)、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州(《补辑石柱厅新志》卷9)、成都市新都(《新都县志》卷3)、重庆市城口(《城口厅志》卷18)相继记载海椒。
从时间上说,以秦椒记载偏早,海椒记载稍后。从地域上说,秦椒记载主要集中在今成都、眉山市一线,海椒则相对分散一些。这些情况表明,四川盆地的辣椒应首先接纳以秦椒为标志的北方传播系统,传人路径具体应有三条:第一,由陕西入川之秦岭蜀道南下;第二,由河南、鄂北沿秦岭南坡、汉水谷道西进;第三,由两湖沿长江西上。后两路应与湖南、湖北中北部相连。记载海椒的方志,同时多称有辣子、辣椒等别名或俗名,与湖南、贵州一线十分接近,应是康熙中叶以来持续“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带来的结果,受湖南、贵州的影响最为直接。《(道光)城口厅志》就出现一个特别称呼:“黔椒,以其种出自黔省也,俗名辣子,以其味最辛也。一名海椒,一名地胡椒,皆土名也。”可见这里的辣椒就主要来自贵州,海椒、辣子一类土名应由移民带来。
正是四川盆地由秦椒至海椒的逐步展开,表明我国明末清初以来辣椒南北两路不同的西进传播在内陆腹地有了一个终极汇集区,同时也标志着辣椒由东向西传播主体过程的大致完成。南北两路辣椒的入蜀,使川渝调味食料在传统蜀椒基础上获得了全新而丰富的辣味资源,促进了川菜嗜辣特色的逐步形成。正是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密切相随,以海椒、辣子等名称为标志的强劲传播,使以湖南、贵州为中心,包括云南、广西大部的嗜辣区得以大幅度拓展,最终形成以湖南、贵州、重庆、四川为中心更大规模的西南嗜辣区,奠定了这一广大区域鲜明而大致统一的饮食传统。
综观这一中南、西南大区食辣风习的形成,除上述湖南、贵州等地自然环境、“湖广填四川”等社会活动的深刻影响外,辣椒本身的食用价值和传播优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辣椒具有相对纯粹、强烈的刺激性,远胜花椒、胡椒等传统辛香之品,“味之辣至此极矣”,食用起来人易成瘾、众趋成风。前引章穆《调疾饮食辩》、佚名《湘侨闻见偶记》从医药、养生的角度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他们的殷切告诫和忧虑显示当时江西、湖南个别地区已经出现一些严重状况。辣椒在这一带多直称辣子、辣火,显然比传统的椒类植物更能满足人们代盐、祛寒湿的客观需求,也更容易令食者习染成风,嗜食不辍。不仅如此,辣椒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种植极为简单方便,产量也十分可观。从下文显示的乾隆以来各地记载看,辣椒品种也趋于多样,兼有鲜嫩蔬用、老熟干品调味等不同用途。底层民众饮食少荤寡味,也更倾向取用。这些都带有更多种植、食用普及的优势。这一带花椒等辛香之品调味的饮食传统十分悠久,尤其是巴蜀地区还是传统蜀椒的盛产地,但清中叶以前无论湘黔,还是川渝都未形成鲜明的嗜辣习性,显然康熙以来辣椒的盛传对这一带食辣风习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独特的自然环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等因素与辣椒自身的种植优势、食用价值综合作用,形成了辣椒在这一广大区域大肆传播应用的历史条件,而包括今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以及与湖南紧邻之江西在内这一辣椒盛传和嗜辣风习盛行之大区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年间的逐步形成,无疑是我国辣椒传播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
上述由山东传至整个北方地区,由江浙闽台至整个华东地区,以及始于广东、湖南的整个中南、西南区的传播发展相继形成了我国辣椒早期传播的三大区系。三大区系不仅是三条各自相对独立的传播途径和分布区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还与当今蓝勇先生所说我国饮食辛辣口味三大分区大致对应。这三大分区是:第一,东起辽东半岛、北京、山东等地,西及山西、陕北关中、甘肃等地的北方微辣区;第二,东南沿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相对忌辛辣的淡味区;第三,长江中上游包括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川以及江西、陕西南部的重辛辣区。明末清初以来我国辣椒的三大传播区系正呈现大致相同的区域格局,分布的疏密与今人食性的浓淡大致对应。其中仅广东、江西的归属略有不同,广东作为中南西南区的源头,自身的辣椒传播分布极为有限,实际分布与今人食用情况都与江浙闽等沿海地区相近。江西虽属华东,早期方志记载也少,但非沿海,境内中南部丘陵山地自然环境与湖南中南部更近,乾隆中叶以来其辣椒食用风气长足发展,品种优势突出,是浙、闽、粤沿海辣椒品种内传的中介环节,因而也逐步融入湖南、贵州、四川、重庆为中心的嗜辣区。当然,笔者所说三大传播区系只就辣椒而言,蓝先生的分区兼辣椒、胡椒、花椒(以麻为主)等多种香辣资源的食用习性。这其中辣椒的传播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仅就这种古今分布的基本对应,也充分表明辣椒进入我国最初200多年的传播发展至关重要,奠定了晚清以來我国辣椒分布及其相应食用风习的区域格局,此后只是向青海、新疆、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海南等外围边远地区的进一步蔓延扩展而已。
六、我国辣椒的来源
关于我国辣椒的来源,有一个前提争议,即我国辣椒是本土原有还是外来物种?我国地大物博,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笔者坚信,如果辣椒原产我国,那么我国文献的记载决不会等到明朝。有关辣椒为我国本土原产的说法,如非有丰富可靠的考古发现作支撑,对明以前文献记载的长期缺失找到合理解释,加上现代生物技术严肃研究的有力证明,任何孤立情景的挖掘都不免有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嫌,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我国辣椒最初必定由美洲新大陆作物传来。在完成上述起源与早期传播状况考述、梳理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国辣椒的海外来源,即我国辣椒从何而来。近代以来,我国方志有“种出西域”的泛泛之言,也有基于现代科学知识的合理推测:“(辣椒)原产于南美热带地方,十六世纪传入欧洲,大约明末清初由南传入广东,辗转传人中原。”但对具体传入来源和路径,不能一味凭空推测,随意想其当然,如所谓经丝绸之路从新疆、由南亚或中南半岛经云贵高原一线传入的说法都了无证据。根据前几节由东到西传播过程的考述梳理,进一步联系辣椒名称和品种记载的先后变化等相关信息,笔者对此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判断。
(一)我国最早的辣椒应来自朝鲜半岛
我国辣椒的最早记载包括农书和方志都见于山东,紧接其后即康熙中叶以前的类似信息出现在其两翼,北边是京津冀至辽宁中部及营口一线,南边是浙江、江苏沿海一线。这种情形最大的可能是,辣椒来源于海东的朝鲜半岛或日本。而据日本著作提供的信息,辣椒传人日本的时间有天文十一年(1542)、天文十二年(1543)、天文二十一年(1552)等不同说法,相当于我国明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三十一年,一说是日本文禄年间即公元1592-1596年出兵朝鲜时带回,相当于我国万历二十至二十四年。朝鲜半岛是世界重要的嗜辣地区,1613-1614年至少有两种文献记载辣椒来自倭国即日本,相当于我国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1614年李啐光《芝峰类说》:
南蛮椒有大毒,始自倭国来,故俗谓倭芥子,今往往种之。显然此时朝鲜半岛传种、食用已有一段岁月。传入时间一般认为是1592-1598年,即我国万历二十至二十六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壬辰倭乱”。
虽然日本和朝鲜半岛双方所说有互为来源的现象,但最终源头都离不开美洲新大陆作物世界传播的过程。日本学者即认为他们的辣椒来自最早闯入远东的葡萄牙人,朝鲜《芝峰类说》称“南蛮椒”,所谓“南蛮”正是明人记载南瓜时所说“南番”,实际所指也是葡萄牙。从时间上说,日本所传辣椒出现时间远早于朝鲜半岛,后者明确的辣椒记载又早于我国《群芳谱》近十年。我国山东、河北、江苏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辽宁又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陆上交通并不复杂。明万历中后期中朝宗藩关系十分亲善,而对倭患则一直积极抵御。因此,笔者支持蒋慕东、王思明先生关于我国辣椒来自朝鲜半岛的推测。但考虑王象晋《群芳谱》和山东方志记载辣椒的时间明显领先,笔者认为我国辣椒最初的起点在山东而非辽宁、浙江,来源也以黄海对面的朝鲜半岛为主,传来方式应是海上,即民间商船、渔船的往来。
当然也有非人为因素传入的可能。人类对辣椒好恶各有不同,猴、鹿、熊等哺乳动物也都惧食辣椒,而禽类却特别喜食。日本著述说,食用辣椒有助于鸟类疗疾。在墨西哥也有同样的报道,鸟类与鸡都喜啄食辣椒,从而把种子带往异地。我国方志也有“鸽性喜吃盐、辣”的记载。实验表明,经鸟吃食的辣椒种子基本都能发芽,而经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所食则不能,“鸟类的消化管不但不会破坏”种子,还会“促进发芽”。明末浙江嘉兴《(天启)平湖县志》记载县东南鄂阳山太子太保屠勋墓“林木翦荟,有鸟从南海来,遥集于上,秋来春去。初至剖其腹,犹有青椒,当是日本国所产”。这类记载不免包含传说和想象,所说青椒更有可能是指花椒、胡椒未成熟的青色果实,辣椒种子在鸟腹内能存续多久也未见有实验报道,但就我国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最近不到250千米的直线距离而言,由海鸟跨海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历城县志》这一方志最早记载说秦椒就是“野蔬”,我国辣椒在山东的出现有可能是鸟类自然传播的结果。《(崇祯)江阴县志》所说番椒如与《群芳谱》相同,又地处江海之交,同属野草,则也可能是海鸟传来。辣椒虽然最初名为“番椒”,认其为外来物种,同时却没有任何传入过程的具体记载和相应说明,在这种情况下,鸟类的自然传播更值得考虑。
辽宁的辣椒记载虽然相对于内地许多地方偏早,但远在山东之后,也在河北之后,更有可能与入清后辽宁沈阳的“盛京”地位有关。两京之间皇室、八旗贵族及相关官员往来频繁,使京津冀地区流行的秦椒得以迅速引至关外的盛京(沈阳)。辽宁辣椒最初也只见于盛京南北的铁岭、盖州一带,而吉林、黑龙江乃至辽宁其他地方的辣椒记载都明显偏后,显然辽宁的辣椒起于盛京,传自关内。明万历中期以来,满洲努尔哈赤势力急剧膨胀,东北各方面形势明显趋紧,辣椒最初由朝鲜半岛陆路传入我国东北的可能性不大。
《群芳谱》所说“番椒”“秦椒”两个名称也值得玩味。前者是文人雅称,后者是民间俗称,“秦椒”一名应更为原始。《群芳谱》主要写作于作者退居山东故乡时,“秦椒”这一俗称最初应流行于山东,山东最早的方志记载也只称秦椒。蒋慕东、王思明先生基于辣椒由朝鲜半岛陆路传入的推测,认为秦椒这一名称可能与东北满语读音有关。笔者认为这一名称更有可能与我国传统秦椒在山东地区的分布有关。秦椒是花椒的一种,与蜀椒并称,《齐民要术》引“范子、计然”说“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秦椒因原产天水等秦国故地而得名。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和宋人《本草图经》都称“秦椒生泰山山谷及秦岭或琅砑上”,反映的是中古时期的情况。所说三个产地中泰山、琅玡山都在山东,可见山东的秦椒分布广泛,由来已久,后世记载渐少,但至少明万历《兖州府志》仍明确记载秦椒。入清后,山东方志中秦椒多指辣椒,而传统秦椒多改称花椒。是山东地区秦椒盛名在先,民间最初接触辣椒,见其辛味如秦椒,遂附名称之,渐成流俗。这与英语pepper一词本指胡椒,后又用以称呼新大陆传来的辣椒一样。在我国,辣椒这样的茄科草本植物最初以木本之“椒”命名,远不如入清后浙人所说“辣茄”来得科学,本就有几分与生俱来的误会,揣度其情景应与辣椒最初落脚在山东这一东部沿海传统秦椒盛产地有关。而作为花椒的秦椒并不耐寒,在辽宁等东北地区生长不利,东部沿海其他地区的分布也不似山东突出,不具备相同的条件,由此也可进一步推证,山东是我国辣椒最早传入地,而其最有可能的来源是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
王象晋《群芳谱》记载辣椒“子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为同时和后来许多著作引用。有趣的是,日本著述中提供了一个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的番椒(辣椒)图片(见图1),椒果正是秃头毛笔下垂的形状,最初经黄海传来我国的辣椒应该就是这种果型。康熙二十九年(1690)林本裕《辽载前集》提供了另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如马乳。”林氏为辽宁盖县人,关外多马,所说比喻带着当地生活经验。同样的比喻也见于乾隆朝松江南汇(今属上海)人吴省钦(1729-1803)《辣茄酱》一诗:“柔尖悬马乳,红影绽初秋。辣爱连皮捣,匀宜着面溲。”吴曾长期在京城任职,马乳之喻应是北方人的话头,说的正是当时北方地区常见的辣椒形状。如果在互联网上以“马乳”检索图片,就会发现所谓马乳正是一个下垂的秃头毛笔样。清中叶前,整个北方地区一路向西的地方志多直接传载“秦椒”之名,几乎不再描写辣椒的形状,所说应多是这种“秃笔头”或“马乳”形状的品种。其中只有陕西方志有一些新的说法,但属于商州等秦岭南坡一带,地理性质上属于南方。这两个比喻之间,“秃笔头”出现早,引用多,而“马乳”之喻不仅出现迟,仅偶然一见,不具先入为主的迹象。《群芳谱》所载这些名称和形状信息带给我们辣椒起源山东,由朝鲜半岛隔海传来的感觉。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以同样的方式从日本甚至由葡萄牙远洋船舶直接传人的可能。至于传入的时间,则应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出现辣椒之后的明万历(1573-1620)后期。
(二)入清后辣椒新品种信息多起于东南、华南沿海,应主要来自东南亚
南方方志的辣椒记载,除王象晋《群芳谱》的影响外,开始就多少有些异样,品种或有另外的来源。康熙十年(1671)浙江《山阴县志》记载“辣茄,红色,状如菱”,名称及形容都与王象晋《群芳谱》明显不同。同样是在浙江,康熙二十五年(1686)《杭州府志》称“细长,色纯丹,可为盆几之玩者,名辣茄”,所谓形状细长,与后世所说羊角品种近似,都是与山东等北方地区秃笔头、馬乳头即秃头圆锥形不同的果型。山阴(今浙江绍兴柯桥)与杭州都在沿海,更有可能入清后从海外直接传人。稍后今陕西商洛市山阳县《(康熙)山阳县初志》记载“番椒:结角似牛角”。牛角、羊角大小不同,但形状应是大同小异,这都是第一批与王象晋《群芳谱》所说形状不同的品种。
乾隆以来,江南南部地区即台湾、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及四川一线有了更多明确不同的品种记载。这一系列品种与先前北方流行的秃笔、马乳形也都明显不同,而且经常多种联袂见载,显然是一个全新的来源和传种格局。最早的是乾隆十年(1745)六十七《台湾采风图考》记载来自荷兰、“实尖长”的木本番姜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实圆而微尖”两个品种。所说来自荷兰的,应是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侵占台湾后传人,但最初应止于台湾岛,传入大陆应在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或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实施统治以来,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辣椒应同属此间或稍早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从西方带来。继而乾隆十六年(1751)江西赣南《(乾隆)会昌县志》记载“形如猪牙”和名为“鸡心椒”两种。乾隆二十二年福建泉州《(乾隆)安溪县志》记载“小如枸杞而微长”的品种,二十四年福建三明《(乾隆)建宁县志》记载“鸡心椒”“朱衣笔”(小而尖似笔),江西抚州南城《(乾隆)建昌府志》记载“圆者为鸡心,锐者为羊角”等。乾隆三十年(1765)杭州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引无名氏《药检》,称“其实有如柿形,如秤锤形。有小如豆者,有大如橘者。有仰生于顶者,有倒垂叶下者,种种不一”。乾隆四十一年(1776)福建厦门《(乾隆)马巷厅志》开始记载黄色品种,广东惠阳《(乾隆)归善县志》记载“有鸡心、佛手,红黄各种”。还有嘉庆间江西章穆《调疾饮食辩》记载的大小、长短、圆棱不一的形形色色品种。
上述这些品种都首先出现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东南、华南沿海以及紧邻的江西,然后逐步内传。在盛产、嗜食辣椒的湖南,乾隆三十年(1765)湘西《辰州府志》称海椒“状如新月,荚色淡青,老则深红”,是羊角、牛角形状的。而同年永州《祁阳县志》的记载是“结实如槐果”,有些方志所说枸杞形,道光间吴其溶《植物名实图考》所绘即枸杞形,都应是今人所说樱桃形的品种。到嘉庆、道光年间,上述这些品种大都传至中西部湖南、四川、重庆、贵州这些喜辣区。所涉地域在北面多止于淮河、秦岭一线,主要在南方地区传种。辣椒易随生长环境、栽培手段不同而变异,因而栽培品种极其丰富。上述康熙以来所传诸多品种或有传入我国后因生长环境和种植技术差异产生的栽培品种,但乾隆以来如此密集出现更多应属异域陆续传来的新品种。揣度其来源,应与台湾“番姜”之类大致相似,主要来自东南亚番国乃至西方远洋殖民者。我国明中叶以来,南洋诸国深受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列强大规模商贸和殖民侵略,辣椒直接传人的机会更多,辣椒传种和品种培育也就相对领先。这些地区与我国东南、华南沿海隔海相望,人员交往频繁,藉此陆续传来极其自然。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由日本、朝鲜方向经海路后续传来的可能。
综上可见,在笔者考察的时间范围内,我国辣椒的传人过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明代后期至清初是第一阶段,主要应由朝鲜半岛经海上传入,品种以秃笔头形所谓秦椒为主,首先分布在山东,进而河北、北京、天津、辽宁一线,主要在北方地区逐步向西传播。康熙以来,尤其是乾隆以来是第二阶段,菱形、牛角、羊角、鸡心、佛手、黄椒等不少新品种在浙江、台湾、福建、江西、广东等东南、华南沿海地区陆续出现,主要在南方地区逐步由东向西传种,其来源则应以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为主,也应包括一些西方殖民者经远洋直接传来。这先后两波的传人,构成了我国早期辣椒传播发展的品种来源,奠定了我国古代辣椒品种的基本结构。
进一步总结全文论述,我国最早记载辣椒的文献不是明浙江高濂《遵生八笺》,而是山东王象晋《群芳谱》,我国地方志最早的记载也见于山东。我国辣椒发源于山东,入清后由此向北、向西逐步传开,所用名称主要是秦椒,在整个北方地区形成了一个时间连续、名称大致统一的传播区。康熙、乾隆年间,以华北平原为核心,包括山东、辽宁等地方志的辣椒记载相对密集,是我国最早的辣椒喜食区。康熙至道光年间,我国南方的辣椒从浙江发轫,时间稍晚于山东,最初多称辣茄,台湾、福建一带后来传人品种则称番姜。整个华东地区早期方志记载比较稀散,显示出大致相同的区域特征。中南、西南诸省区的辣椒记载更在稍后,但大多比较密集,传播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湘西的辣椒记载早、分布密,最初多称海椒,应来自广东沿海。深得苗、瑶等少数民族生活风习传布和“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推动,又适应一些缺盐、瘴湿环境民众的特别需求,由此先后向南、向西强劲传播,最终形成以湖南、贵州、四川、重慶为核心的广大密集分布区。四川盆地的辣椒兼得南北两个方向的来源,有着南北两路终极汇流的色彩,也标志着辣椒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传播主体过程的基本完成。上述三大区固然起始时间有先后,但更多是辣椒名称、传播关系、分布疏密的不同分野,奠定了我国晚清以来辣椒不同食用习性的区域格局。根据上述辣椒起源、传播情况及相关品种信息,我国古代辣椒的传入分为两个阶段。最早的辣椒应来自与山东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传入时间在明万历后期。辣椒这样的茄科草本植物在我国以木本之“椒”命名,应与最初落脚在传统秦椒分布较盛的山东有关。清康熙尤其是乾隆以来,浙江、福建、台湾、广东等东南、华南沿海及相邻江西等地多有不同新品种陆续记载并逐步内传,其来源则应以东南亚为主。
(责任编辑:来向红)
- 双切口钢板法治疗复杂胫骨平台骨折患者的效果
- 微型钢板内固定治疗后踝骨折的临床效果
- 雷替曲塞联合奥沙利铂与FOLFOX4方案对晚期结直肠癌临床综合疗效及安全性比较研究
- 锁定钢板内固定加植骨术与钢板内固定术治疗跟骨骨折的价值
- LCBDE治疗胆囊结石并肝外胆管结石的效果
- 丙戊酸钠联合利培酮对癫痫性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功能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 低能量强脉冲光影响C57BL/6小鼠毛发生长的实验研究
- TPRK术中应用眼球自旋控制功能矫正近视合并中高度散光的临床研究
- 氨磺必利治疗精神分裂症对患者催乳素及糖脂代谢产生的影响研究
- MIS-TLIF与W-TLIF治疗单节段腰椎椎管狭窄症的临床效果分析
- 早期CRRT在脓毒症治疗中的应用及疗效探究
- 应用中医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虚证研究进展
- 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 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研究进展
- 碘131和抗甲状腺药物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进展
- 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改善的护理干预研究进展
- 气压治疗联合产后康复按摩预防高龄产妇剖宫产术后DVT的临床研究
- 循证医学模式联合PBL教学法在肿瘤内科教学中的应用
- 三级防控理念对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行为及脂代谢的影响
- 25-羟维生素D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分析
- 分娩体验教育对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
- 品管圈活动用于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加速康复的效果评价
- 老年男性体检人群心理问题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碳水化合物计数法干预应用于T2DM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效果分析
- 孕妇妊娠晚期B族链球菌检测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 tear¹
- teas
- teasable
- teasableness
- teasablenesses
- tease
- teased
- teaser
- teaser ad
- teaserad
- teaser rate
- teaserrate
- teases
- teasing
- teaspoon
- teaspoons
- teat
- teated
- tea towel
- tea towels
- teats
- tech
- techheavy
- techie
- techies
- 美好的音乐、言论、作品等依然存在,并未消失
- 美好的韵味风格
- 美好的风土诞育优秀人物
- 美好的风姿
- 美好的风尚和教化
- 美好的风度
- 美好的风格韵味
- 美好的风范
- 美好的风范永远留存
- 美好的食物
- 美好盛大的样子
- 美好秀丽
- 美好精妙
- 美好精致
- 美好繁多
- 美好细腻
- 美好绮丽
- 美好而坚贞
- 美好而崇高
- 美好而幽静
- 美好而新奇的构思
- 美好而有光泽
- 美好而柔婉
- 美好而茂密
- 美好而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