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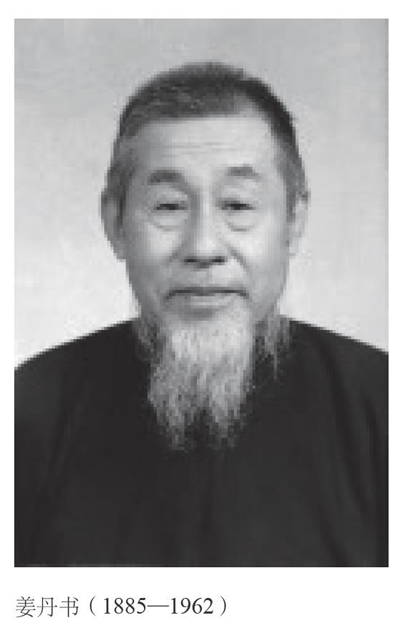


【摘 要】 20世纪初,源于“人物品藻”传统的中文词“三杰”被用于对应并翻译文艺复兴“三大艺术家”这一外来概念,从而与“拉斐尔”在中文语境中的传播历史发生紧密联系。该词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写作挪用传统语汇阐释拉斐尔等外来概念,调和古今矛盾,融汇中西传统的话语创新。“拉斐尔”“三杰”“文艺复兴”等概念在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是艺术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文化信心,参与救亡图强,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重要话语媒介。简明而兼容的语言特性推动了概念的流行,同时也限制了对艺术史实的深入认识。分析这些概念的传播,有助于厘清中国艺术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文化信心的过程。
【关键词】 拉斐尔;三杰;文艺复兴;概念传播;艺术史学史
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人物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他的声名又与“三杰”概念紧密相连,有关其生平、个性、代表作以及艺术特长的表述往往都被纳入这一系统。这种概念式的书写固化了拉斐尔的形象,且使得人们的注意力仅被集中在少数作品上,从而忽视了丰富多样的历史事实。本文借助雷吉斯 · 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生成的螺旋”[1]理论,从拉斐尔在中文语境中的接受史入手,梳理20世纪上半叶艺术写作中的相关内容,讨论“三杰”概念引入、确立、流传过程中的社会和思想因素,从话语角度反思艺术史学史中的传播问题。[2]
“拉斐尔”与“三杰”的迻译
“拉斐尔”一词于20世纪初被引入中文世界,它首先出现在一些翻译和介绍性的写作中,后随着民国初年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出现在艺术类通用教材里。一些作者的个人观点通过教育系统迅速传播到教师和学生之中,又借助大众媒介引起广泛的关注。通过对中文话语历史的追溯,可以发现“三杰”被挪用到艺术写作的历史反映了中外文化交往的复杂性。
“拉斐尔”这个名字是西文音译,乔尔乔 · 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传记中明确提到,它有“良好的祝愿”之意。[1]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犹太民族,后作为基督教中大天使之名而广泛传播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此名在天主教经典《多比传》(Book of Tobias)中有载,今天被汉译作拉弗尔或辣法耳。但它作为艺术家名字先后出现过拉飞尔、拉法爱尔、拉孚挨鲁、拉弗挨尔、拉费尔、拉飞耳、拉斐耳、拉法艾耳、拉华尔罗、拉腓尔等多种译法。[2]拉斐尔这一译法最早见于1922年,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译名都不统一。[3]
早在1904年,拉斐尔就被介绍到中国。康有为变法失败多年之后前往欧洲考察,他将考察见闻写成游记发表,欲以“万国之华实”为药方医治“中国之病”。[4]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详细记录了所见拉斐尔画作,并对其大加赞赏,称“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生气远出,神妙迫真”[5]。他每遇拉斐尔作品必然记录,在游记中他还写下八首绝句,将拉斐尔的绘画与“太白诗词右军字”相提并论,赞颂其创新改革绘画的“作纪新元”之功。[6]对于康有为来说,近世拉斐尔所代表的西方绘画传统超越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失去优势的表现之一,他说:“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7]在拜谒万神殿拉斐尔墓之后,更感叹“意人尊艺术,此风中土甚惭焉”[8]。康有为对拉斐尔的认识有不少来自见闻直观,也有一些不准确的信息,但是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绘画的有识之士,他深刻感受到文化差异和冲击,并将这种感受融入到自己力求变法革新的政治诉求合理性中。有趣的是,康有为非但未使用“三杰”之名,甚至连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作品也没有谈到。
稍晚时清末外交官钱询的夫人单士厘随丈夫遍游亚欧各国,将自己的见闻著为《归潜记》,于1910年家刻出版,她将拉斐尔译为拉法爱尔。[9]在其游记中,拉斐尔并未被冠以“三杰”之名。从原文丰富的注释可知,作者写作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外文材料,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其见识深刻、准确。
对拉斐尔的整体介绍最先出现在新型教材中。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师范教材《美术史》。作者姜丹书在介绍文艺复兴艺术时写道:“当时地方派中,以佛棱斯之米启兰启鲁、拉孚挨鲁、列阿纳多为支配时代之三大家,史称意大利三大画杰。”这一论述可以看作中文“三杰”说的最早版本之一。在姜丹书的笔下,拉斐尔是作为米开朗基罗的竞争者出现的,是一位“集大成兼众长”的“调和家”。[1]姜丹书又在同年出版的《美术史参考书》中称“拉孚挨鲁氏实千古之画圣”[2]。姜氏此书开中国学者写作外国美术史的先河,据原序作者桂绍烈介绍,作者“博访周咨于中外作者,成美术史上下二卷”[3]。整体而言,如穆瑞凤所指出的,姜丹书编写的西洋美术史部分受到日本学者影响。[4]且姜氏对拉斐尔的译名非常接近日文读音。由于此书并无注释,无从确定他对拉斐尔的评语是作者个人观点还是借鉴他人定论。但是姜氏将世界美术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系统,对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别艺术史有所剪裁,说明他意欲使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抗衡”。因此我们猜测,他将拉斐尔列入“三大画杰”并评为“画圣”,很有可能是为了对应中国“六朝三大家”以及“画圣”吴道玄的评论。[5]这样既使得东西方历史图景互相对称而完整,又符合他所谓艺术的极盛产生于摆脱“中世”宗教的观点。
假如姜丹书的评价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借鉴了外国学者的说法,那么这种东西并立的观点,显然带有强烈的日本因素,尤其可能受到冈仓天心对亚洲文明一体性论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姜丹书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的图画手工教员一职,正是接替日籍教师吉家江宗的位置。[6]1912年,李叔同亦应聘来校,与姜丹书同在图画课任教,二人过从甚密。李叔同恰好毕业于冈仓天心曾经筹办并任校长的东京美术学校。中文“三杰”一词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借用了日文文献中的表述呢?
日本虽然存在“文艺复兴三大艺术家”的说法,但这并非严格的学术概念。20世纪初的“三杰”之说则更多出现在关于政治人物的历史和文学语匯中。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最广为人知的“三杰”是由传记文学所建构起来的“维新三杰”或“十杰”等说法。[7]当时中日两国作为文化背景相似的近邻,又同样有革新图强的历史诉求。因此“维新三杰”在19至20世纪的东亚舆论中,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流行话语,虽然其内容是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但却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出现,朗朗上口,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然而这并不是“三杰”一词在中文文化圈内的最早案例。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三杰”话语的重要源头之一是《汉书》中汉高祖称赞张良、萧何、韩信三人的评语:“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8]此后,“蜀(汉)三杰”“南宋三杰”等一大批类似模式的中国历史名人组合频繁出现在史学、文学和各类通俗读物中。在20世纪初的中文报刊中,“汉三杰”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维新三杰”。各类报刊媒介套用此种人物品藻的模式,对当时国内外政治人物进行类比评价。尤其是那些辅佐君主扭转落后局面的政治人物,受到中国思想界和普通读者的关注—这既是清末对维新变法的舆论鼓吹,也是开拓中国读者眼界的热门话题。这个词甚至被挪用在外国人物身上:新近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变法图强的日本、大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成为“三杰”辈出之地。其中,梁启超于1900至1903年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可以被看作一次在欧美人物身上运用“三杰”模式的大型实践。在这段时间里,“俄廷三杰”“美利坚建国三杰”等说法纷纷出现。人们甚至将清末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赞为“中兴三杰”,又进而组成“欧亚九杰”。[9]在媒体上俨然已经形成东西两洋并立,中外平衡,各自走向中兴的舆论局面。
“三杰”一词在脱离原境的流行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人数和领域不一的变体,如“爱尔兰四杰”“陶界三杰”“党人三杰”等,不一而足。该词流行于对银行界、歌舞界、戏剧界、艺术界人物的评论中。而用于对文艺复兴“三大画杰”之一拉斐尔的评价正是此种泛化的结果之一。姜丹书的看法无论是否直接借鉴自日文文献,20世纪初,中日语境中大量为人熟知的“三杰”表述都促成了从“三大画杰”到“三杰”的简化,而且这种简化显然适宜中文语境中刚刚起步的外国艺术史写作和艺术普及的需要。
“三杰”与民国“文艺复兴”热
在西方,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视为艺术中三位并列的最高代表的观念并不来自于文艺复兴,也未见于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之间的写作。这是一种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流行于19世纪初的现代艺术观,它与将艺术活动视为人的创造能力的表现这一启蒙观念有关。
而在中国,作为政治和文学用语的“三杰”被挪用到艺术领域的同时,该词被中文和日文写作者用来对译西文材料中的上述表达,从而形成今天的“三杰”概念。然而这个概念确立的过程是动态的,与国人寻求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的心路相契合。1920年,适逢拉斐尔逝世400周年,借此契机,中文媒体上出现了对拉斐尔生平和创作的专门介绍,同时也引发了国人对“文艺复兴”概念的兴趣。这种兴趣亦反映出中国思想界不甘落后于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模式中寻找旧邦维新的史实与理论,以便支撑对传统文化的信念。译介各类有关“文艺复兴”的材料,不仅是艺术界人士的兴趣所在,还与启蒙救亡的历史潮流相吻合,在20世纪上半叶引起不同立场的各社会阶层关注。
1920至1921年,丰子恺在《美育》杂志上连载文章介绍三位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文章标题和开篇第一句都强调了“三大画杰”这一概念,指出这三位艺术家空前绝后的天赋。丰子恺以“画杰”称之,说明着眼于批评画坛人物,需要以此区别于当时常被称为“杰”的政治人物,也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等领域的杰出人物。然而丰子恺认为“三人者,盖创造文艺复兴期者也”[1],又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丰子恺沿用拉斐尔传记中所记载的说法,称拉斐尔模仿老师画风“无不酷肖,见者不能辨别之”,画技高超令竞争者嫉妒而死,以及37岁英年早逝等细节,塑造出生动而传奇的天才形象。[2]丰子恺对艺术史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任教于中学时期所编纂的三本出版于1928年代的讲义:《艺术概论》《现代艺术十二讲》和《西洋美术史》。丰子恺擅翻译,长于多国语言,据后人回憶,前两种著作翻译自日本作者,后一种则出自编译。《西洋美术史》中有“文艺复兴期三杰”一节专门介绍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在丰子恺看来,达芬奇“神秘”;米开朗基罗是三者之中最伟大者,是“英雄的范型”;而拉斐尔则是“薄命的”“讨人欢喜的”“通俗的”。[3] 1930年,他还曾经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更详细地介绍这几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在这些文章中,丰子恺不仅强调了“文艺复兴三杰”这一概念,还借佛教用语,将达芬奇和扬 · 凡 · 艾克(Jan Van Eyck)分别称为欧洲南北的“第一代画祖”。[4]十年之间,“三大画杰”变成了“三杰”,反映了术语的固化。丰子恺对文艺复兴的写作重点突出了英雄型人物的性格,他对拉斐尔的塑造方式体现为将其视为“三杰”框架中人格和艺术之一极,此框架的特点是将三者的艺术看作“求真—求善—求美”三元关系的表现。通过丰子恺的写作,拉斐尔英才早逝的形象深入人心,其人性和艺术特点突显了纯粹的审美价值。
与丰子恺同时开始介绍文艺复兴的,还有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字百里,以下称蒋百里)。1921年,蒋氏将早年访欧见闻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引起极大轰动,14个月内共发行3版。蒋百里虽然专研军事,然而对欧洲历史、文化、艺术有独到见解。其书对意大利、法国、北欧国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都作了介绍,并指出欧洲借由复古潮流而产生新理性的“社会蝉蜕之情状”可以为中国所借鉴。蒋氏在书中谈到文艺复兴有文学“三大人物”,而艺术中“其大师有三:曰文西,曰米格安治,曰拉飞耳,三人者各有独到之能……文西之艺术源于知,米格安治之艺术源于力,拉飞耳之艺术源于爱”。[1]在蒋百里的评价中,并未直接使用“三杰”字样,而以“三大师”称之。时人认为此书“取材于法人白黎许的演讲”[2],从内容来看,温克尔曼(蒋译“温格孟”)的学说、布克哈特“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的观点,以及当时多位德语学者提出的欧洲南北文化对比论的观念都对蒋百里产生了影响。蒋百里在《总论》中特别指出,研究文艺复兴需注意三点:“一不可有成见”“二不能专注重伊大利”“三不可专注意美术文学”[3],此见解可谓高屋建瓴。因此,在他谈论意大利艺术的部分时,并未受“三大师”的限制,不仅详细论述古典文化的影响,还介绍了13至15世纪的不少艺术家及作品。蒋百里用“心灵与肉灵调和”“纯洁”“高尚”“通俗”“亲切”“有女性(特征)”等词汇概括拉斐尔的艺术特点。[4]由“知、力、爱”三元所构建的“三杰”艺术框架显然是哲学中的“真、善、美”和心理学中“知、情、意”三元关系的同构。在蒋百里观念中,“三杰”一词的合理性在于其结构暗合认识论和心理学的一般观念,引人联想,易于接受。在这一点上,蒋百里和丰子恺有异曲同工之处,用这个三元关系勾勒出拉斐尔的道德形象和艺术特征。
蒋百里书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引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5]梁启超将清代比作欧洲文艺复兴对应历史阶段的看法更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学术界对文艺复兴的兴趣,从之者甚众,而反对者亦有之。1929年,哲学家谢扶雅发表两篇文章对梁启超加以批驳。[6]姑且不论梁、谢二人观点是非,仅从文艺复兴话题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中文语境中的流行现象来看,报刊上有关中国文艺复兴话题的讨论逐年增多,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达到顶峰。抗战期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局势的恶化,这一话语又被日本势力所利用,以鼓吹亚洲文化崛起来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例如:20世纪40年代,中日文化协会大力推行所谓“东亚文艺复兴运动”;1942年11月,以川端康成为首的日本作家又在东京召集“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组织多国文学家讨论“东亚文艺复兴”等议题。[7]
总的来看,“三杰”和“文艺复兴”等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进入国人观念的过程中,不仅脱离其原本的语境,更被赋予许多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想象,甚至为各种势力所利用而成为特定政治诉求的外衣。
“三杰”概念的传播与反省
丰子恺勾勒出拉斐尔英年早逝的天才形象,而蒋百里则奠定了中国人心目中拉斐尔艺术可亲可爱的特征。此二人分别从日本和欧洲接受了“三杰”说,有不少后来者或以之为材料来源,或借鉴其观点。[1]
在各类报刊媒体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三人成为了从绘画领域扩大到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用语的评价色彩也变得更强烈。[2]“三杰”说也和一些“不标准”的说法同时存在,如“四大名家”“二代表”“艺术三杰士”[3]。从时间上来看,报刊上的“三杰”说法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三杰”用语逐渐固定,并在40年代得到广泛而稳定的使用,画家陈之佛、许幸之、王琦都曾撰文。[4]不少流行画报还刊印“三杰”作品的照片。[5]艺术家的写作和可视化的艺术图像的传播都推动了此概念的扩散。
艺术家的写作对“三杰”概念的固化与推广起到极大的作用,不少观点还影响到20世纪下半叶的拉斐尔研究。1925年,身陷裸体模特风波之中的刘海粟评价“拉飞尔”等三人“空前绝后”,他沿用蒋百里对三人“爱也智也力也”的归纳,赞美“人类之特性”,这既有以西方艺术史为自己摆脱道德指责的辩解,又有他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大师”的自我期许和标榜。[6]后来艺术家的发言屡见不鲜:张充仁宣传拉斐尔“仕女美而不俗”,价格昂贵[7];陈之佛强调了拉斐尔作品“女性的资质……优美胜于力强”,其人则是“缩命的天才画家”[8];左翼版画家王琦评价拉斐尔“一生和苦痛或反抗绝缘……只有快乐而没有苦恼”[9]。艺术家使用“三杰”这一带有褒义和强烈情感色彩的评语,既是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又是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的认同。这个词汇既可以将西方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与中国古代品藻传统结合起来,同时又和“文艺复兴”概念一同强调艺术与艺术家对现代社会和国家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对拉斐尔等外国艺术家身份的重新塑造,中国的艺术家们在与传统的“文人画家”身份相切割的同时,也摆脱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保守落后形象的困扰。“三杰”的提出和确立,可以看作艺术家群体对美术革命的反思和应对,通过将“三杰”这一传统品评用语嫁接到“拉斐尔”和“文艺复兴”等外来艺术概念上,不仅与“革命”的对象划清了界限,还转而成为先进社会力量的“杰出”代表。
概念化的理解常常会导致历史认识和叙述的简单化,因此逸闻趣事、传奇误解成为丰富简化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高昂的艺术品交易价格,艺术家之间的竞争与弟子为师傅复仇的各类故事,甚至误用艺术家名字、原文及肖像对于大众媒介来说都无伤大雅。[10]类似“三杰”式的评语如“画圣”“圣手”“怪杰”也相当流行。[1]拉斐尔“为人幸福”,作品“美而不俗”“尽是快乐”等评价使得他在“三杰”框架中稳固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面对“三杰”说也显示出极为谨慎的态度。1923年,陈衡哲所著《西洋史》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书是中学教科书之一,曾经产生很大影响,三年之内六次再版。陈衡哲在序言中指出,欲以历史研究揭示西方文明的真正要素,揭穿武人政客愚弄人民的黑幕,因此对西方文化尤为感兴趣。[2]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时,她说:“达芬奇、米开兰基罗,及拉飞尔三人为最杰出”,认为拉斐尔“有第一等的天才”,能够将“意大利所有美术家的佳处……调和运用”。[3]在陈衡哲的视野中,文艺复兴是一项影响欧洲各国的广泛运动,其成就包括古学、文学、艺术、科学,而艺術又含建筑、雕刻和绘画,每一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因此研究不应拘泥于艺术,更不能以绘画概括全部。她认为拉斐尔仅成就于绘画,而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则是雕塑和绘画两门中的代表,并以拉斐尔圣母像为例证强调文艺复兴在绘画技术、范围和审美三方面的发展。她虽然使用了大量的“杰出”“天才”字样,显然并非要作标签式的概括。这种视角也体现在她1926年的《文艺复兴小史》中。此书重复了《西洋史》的框架和基本观点,但是在列举绘画领域“第一等的人物”时,却选择了“其中最杰出的四位”— 达芬奇、米开兰基罗、拉斐尔、提兴(提香)。[4]可见在中文“三杰”概念提出之后不久,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它的局限性。
实际上,只要试图对文艺复兴艺术加以全面介绍,就难以使用“三杰”概念。因为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所活跃的时间、地域、艺术门类都不尽相同。而且,从连续的历史视角来观察,就会发现这三位艺术家的成就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及传承有关,难以用充满浪漫色彩的绝世天才的想法蔽之。1928年,萧石君的《西洋美术史纲要》将建筑、绘画、雕塑三种不同艺术类别分开著史,只在绘画中先后提到这三位画家,并称为“支配中部意大利地方的作家”[5]。这种分流派讨论的写法是18世纪末以来欧洲艺术史的常见叙述模式。1933年,吕澂在《西洋美术史》中也并未采用“三杰说”,而是将达芬奇和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柯勒乔分开两节论述,将其视为不同地域和历史阶段的代表。[6]而画家倪贻德虽然也有留日经历,但在他的《西洋画派解说》中,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被看作文艺复兴历史上的不同阶段,米、拉二人则被称为艺术上“确定的胜利者”[7]。
此外,拉斐尔前派及其批评家对拉斐尔的指责所引发的争论也被翻译到中国。[8]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937年李朴园译赖那克的《阿波罗艺术史》,这也是当时较为系统的艺术史译著之一。赖那克将拉斐尔的柔美愉快风格艺术放在翁布里亚、佩鲁贾、锡耶纳等地方画派的传统中看待,用颅相学观点解释他作品流露出的女性气质,并将17世纪之后“艺术的颓唐”看作在拉斐尔影响之下的结果。[9]在这部著作中,达芬奇、拉斐尔(李译“拉腓尔”)和米开朗基罗被看作意大利不同地方的艺术流派代表,被分别放置在不同章节讨论,但未见作者以“三杰”字样称之。可见,随着对文艺复兴讨论的深入,历史面貌得到不断的揭示,“三杰”概念的局限性愈发明显。但对于艺术普及和大众传播等目的的写作来说,简单概括和高光式的介绍显然是更容易的选择。
总的来说,当中国人开始了解拉斐尔和文艺复兴艺术之时,西方艺术史中的“三头”(triumvirate)或者“三大师”(three great masters)等概念通过翻译被介绍到中国,并与传统语汇中的“三杰”相结合。拉斐尔进入国人视野的途径主要有二:第一,来自姜丹书、丰子恺等与日本美术界关系较为密切的中国作者或对日本作者著作的翻译介绍;第二,来自康有为、单士厘、蒋百里等人的旅欧见闻。这两种途径中的基本观点都将拉斐尔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一同视作文艺复兴的代表。
结论
“三杰”原本是19至20世纪之交中日两国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学中品藻政治人物的用语,这一概念很可能源于中国历史典故“汉三杰”,它在被报刊等现代媒介传播的过程中,脱离自身语境,被泛化并被挪用到普及文本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开始关注拉斐尔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艺术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结束后不久,民国初创,政治动荡时期。国体的改变并未带来社会现实情况的好转,介绍外国文化符合洋为中用的舆论期待。在诸多作者中,艺术家的写作是推动“三杰”概念传播的重要力量。这个概念使艺术家从“美术革命”的对象中解放出来,在保留古代品评用语和部分价值观的同时与西方艺术传统相接轨,帮助艺术家摆脱保守落后的“文人画家”形象,塑造了现代的、进步的、肩负民族历史使命的新型艺术家身份。它包含强烈的英雄崇拜意味,契合了现代转型、寻求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中国读者对天才人物的渴求和对国家迅速崛起的期待。传统语汇的基因注入外来概念所产生的新意涵因而获得了巨大的生机,承载了接受者自身文化的一些特征。“三杰”框架中的三个艺术家分别代表不同的人格特点和艺术特色,“智、力、爱”三元构成类似于“真、善、美”或“知、情、意”的概念框架。詞汇层面的跨时代性、跨语境性、简明性、普适性为概念的广泛传播打下基础。
与“三杰”概念同时传播开的另一概念“文艺复兴”,在梁启超等人的鼓吹下被赋予文化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它先后成为保守主义者、中华民国政府和抗战时期的日伪势力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也脱离自身的历史语境,与“三杰”概念的演变路径恰好相反,从异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之内。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华民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增强,“三杰”这一明显具有传统人物品藻特点的中式语汇大为流行,“文艺复兴”概念被其用作对国家进行民族化塑造的文化标签,变得简单化、脸谱化、本土化,并在传播中被赋予民族主义的色彩。而这类概念同样也被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和伪政权所利用,被赋予别样的民族想象。
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美术学院刘晋晋、文韬、王浩以及北京大学祝帅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 名角儿的魅力
- 人性美·耀人间
- 浅谈当今戏曲舞台布景的发展及应用
- 论山东地区传统戏曲创作的艺术实践探索
- 个人意志与既定命运的对抗
- 古老的传承
- 以陌生化理论视角评德国邵宾纳剧院版《理查三世》
- 舞蹈治疗对中老年群体的影响
- “情景再现”创作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应用研究
- 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包装与品牌形象塑造
- 当今电视晚会中的喜剧小品节目现状分析
- 中国第五代导演分析
- 电影《黄金时代》的“间离”叙事解读
- 浅议体育电影中阐释的美学意义
- “他者”视域下的自我成长
- 网络影视评论的传播机制与社会功能
- 分析《我的前半生》与《伤逝》新旧子君命运不同的原因
- 从仪式角度看不确定性回避理论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 看《唐顿庄园》中英国社会的变迁
- 解读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中声音的作用
- 浅析虚拟偶像的定位及与其它动漫形象的区别
- 《心迷宫》:多层视角下的人性拷问
- 在角色的生命中成长
- 浅析中国动画结合中国传统艺术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
- “互联网+”背景下微电影广告的传播研究
- semicolloquial
- semicolloquially
- semicolon
- semicolonially
- semicolons
- semi-column
- semicomical
- semicomically
- semicommercially
- semi-commoner
- semicommunicative
- semiconcealed
- semi-conductor
- semiconductor
- semiconductors
- semiconfinement
- semiconfinements
- semiconformist
- semiconformists
- semiconformities
- semiconformity
- semiconically
- semi-conscious
- semi-conservative
- semi-conservatively
- wā
- wāi
- wān
- wāng
- wēi
- wēn
- wēng
- wěi
- wěn
- wěng
- wěnɡ
- wō
- wū
- wǎ
- wǎn
- wǎng
- wǎnɡ
- wǒ
- wǔ
- wɑ
- wɑi
- wɑn
- wɑng
- wɑnɡ
- w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