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在日本的困境和没落
张跃斌
实证主义曾是日本史学界的圭臬。但是,近年来,由于日本侵华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在日本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实证主义遭遇了三重困境:禁地难入、过犹不及、以假害真,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学术后果和社会后果。
DOI: 10.19422/j.cnki.ddsj.2016.12.012
在日本的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实证主义最为盛行。早在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就从西方引入了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此后逐步发展成为学界的圭臬。可以说,“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是明治以来的主流”。实证,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事实来进行论证”,而事实,则是通过史料来呈现的。显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对历史事实的挖掘和考证是历史学的第一步,也是基础性的一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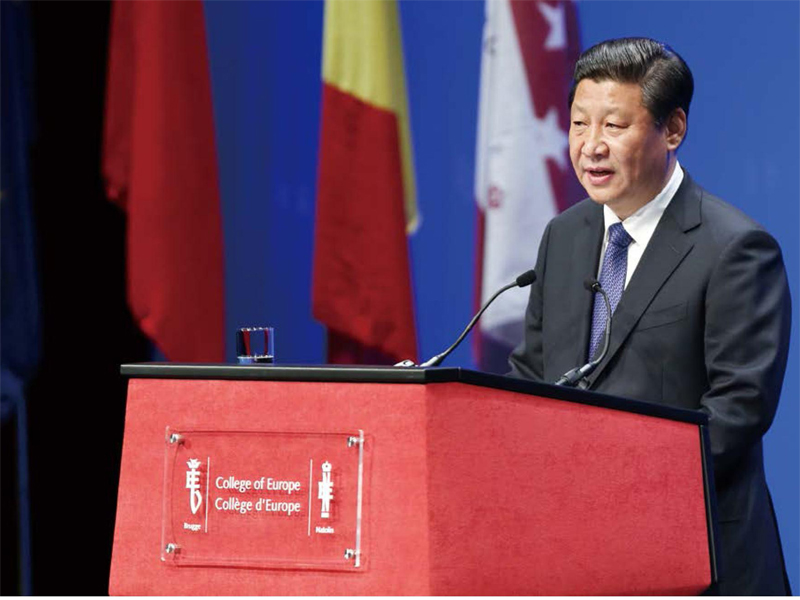
实证主义曾经是日本学者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近现代日本历史研究的实情来看,实证主义已是气息奄奄,举步维艰,俨然成了日本历史学界的尴尬和难堪。总体上看,在日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中,实证主义遭遇到了三重困境,或者说三重障碍,并由此表现出没落的迹象。
困境一:禁地难入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学术研究受到重重限制,学术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其中一些领域是学者研究的禁忌,如日本皇室的历史。因此,关于日本的早期历史就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神话、传说被当作客观存在的史实,成为统治阶级借以愚弄民众的工具。
近些年来,在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和氛围。也就是说,在研究中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了一片禁地,令研究者望而却步。20世纪末,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南京大屠杀问题、“731”细菌部队问题、慰安妇问题、强制劳工问题等等,在日本学界和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十分吊诡和遗憾的是,通过争论,不仅没有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反而使这些研究领域渐渐成了学术的禁地。时至今日,很少有学者敢于将实证主义精神运用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在为数众多的各种专业历史学杂志、著作中,有关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但数量很小,和其重要性完全不成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难道学术争论不是愈辩愈明吗?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学术争论取得了最终的结论,从而使一方偃旗息鼓,而是学术研究遭到了政治力量的蛮横干预。国家权力的打压,右翼势力的恫吓,逐步营造出一种氛围:真正的学术远离和退却,而虚幻的国家自豪感则堂而皇之地回归到历史叙述和研究之中。
一些日本学者一直标榜学术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然而,偏偏在上述问题上,学术问题关系到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不同的学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看到,一些学者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既追求学术的真理,也追求政治的公正。不过,也有一些学者退缩了。他们将引起争论的学术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于是,本着所谓的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原则,他们就为自己游离于这些研究课题之外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不仅如此,他们还制造舆论,逐步营造出阻挠其他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氛围。
作为一名学者,笠原十九司对相关的学术问题持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并积极发表意见来影响普通大众。不过,笠原个人的境遇却反映了学术界的现实。在历史研究者中间,他被贴上了市民运动派的标签。也就是说,一些学者暗示,笠原的研究不是学问,而是带有政治运动性质的,因而学术价值很低。这些学者认定,学者应该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保持距离,采取“中立的、非政治”的立场。应该说,笠原的遭遇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关于日军“慰安妇”等战争犯罪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进展。可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国内历史研究的重要团体之一),“一贯漠视慰安妇问题。不仅是慰安妇问题,关于战争犯罪、战争责任问题,他们几乎都视而不见”。这表明,日本的一些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不是选择探明真相、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而是选择逃避。
学者提倡学术的独立性,这本来无可厚非,学术研究也需要这样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在于,当政治力量野蛮地干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的时候,一些学者无心恋战,随便应付一下,便缴械投降,之后还自欺欺人地说,自己不做和政治有关的学术。只要是国家不同意的说法,只要是引起争论的话题,他们就将其抛入政治问题的领域,从而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政策。只是,这样步步退却,最终丢掉的将是自身的存在价值。在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实证主义正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还原历史的真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不护短,直面本民族的错误和弱点,从而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可是,在虚幻的民族自尊心的威慑之下,实证主义悄悄地后退,为日本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行径让出了舞台。
困境二:过犹不及
在学术研究中,实证主义是必要的,但也必须适度,从而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但近些年来,日本学界的实证主义,尤其表现为过度琐碎的实证主义,妨碍了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不能否认,大量的实证主义者成果卓著,他们的精神感人至深。日本学者永原庆二说过,“‘实证主义的研究者视个别认识为历史学压倒一切的任务,坚韧不拔地埋头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证,无所畏惧地不懈努力,力图搞清楚史实的每一个细节”。同时,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队伍的壮大,考证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改进,日本的实证主义在战后获得了极大的进展。这样,通过新的考证技术搞清了以前不明白的个别事实,实证主义历史学就在学问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也必须看到,近些年来,一些因素也促使实证主义研究出现过度的倾向。一是研究机构对学者研究数量的要求过于刻板。日本学者承认,“在业绩至上的风潮中,相较于从整体上讨论历史研究的社会作用,严密的实证研究更受重视。结果,历史研究越来越细化,历史的整体脉络也越来越难以认识”。二是如前文所述,一些历史学者自我设限,退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既然他们不能不对一些研究领域敬而远之,那么必然在另外一些研究领域投入过度的时间和精力。十分可悲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能研究的领域正是近现代历史的核心领域和重要领域,如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及其相关问题。而能够研究的很多问题则是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领域。
如此,就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后果,日本的实证主义研究越来越精致,但是距离真理却似乎愈来愈远。日本学者在谈到学界对战争期间“政军”(指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研究时评论道:“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越来越精致,虽然其本身很重要,但也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充分说明研究的意义所在。”确实,过度的实证主义研究不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不缺乏精致的研究、细微的研究、专业的研究,缺乏的是宏大的研究、深入的研究、触及事物本质的研究。在这方面,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曾经提出过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思考和领会。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学家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 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摒弃。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在论述历史学家的“史识”时也强调:“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这些论断,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关键,也指出了历史研究的精髓之所在。
一些研究者在实证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大量的研究陷入琐碎的历史史实的考证之中,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过分专业化的领域,与日本的社会现实需求渐行渐远,大面积脱节,正在沦落为某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这些实证主义研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的,逐渐陷入了自娱自乐、自我封闭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研究的悲剧。
困境三: 以假害真
许多学者对于敏感的课题唯恐避之不及,害怕卷入所谓的政治之中。可是,还有一些学者,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屡屡就相关问题发声,并且在日本社会很是吃得开。秦郁彦,日本近现代史的所谓“学术权威”,被奉为“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如此。2014年,日本右翼打出了所谓“历史战”的概念,要与中韩在历史领域进行对决,秦郁彦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秦郁彦的得势,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观点和日本政府、日本右翼相同或者相近,受到他们的赏识;二是他顶着“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光环。那么,秦郁彦的实证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实证主义呢?实际上,秦郁彦的实证主义乃是地地道道的伪实证主义。
所谓的伪实证主义者,就是经常给别的学者扣上非实证主义的帽子,自称自己才是真正实证主义的学者,而完全不顾自己违反实证主义精神的事实。例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秦郁彦称自己才是客观、公正的,对于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他字里行间影射中国政治干涉了学术,口口声声要让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回归学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的所谓研究正是日本政治影响下的产物,只不过是以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自居而已。秦郁彦在其《南京事件》(2007年增补版)一书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中国人总数为4.0万人,并且强调“该数字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新史料而留有余地的,因而可以说是最高的估计数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实证主义态度,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会下如此的结论。同时,在他的论述里,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却武断地声称中国证人的数字都是夸大的。可见其论述的套路其实是先有“结论”,然后根据“结论”来选择和解释材料。
在慰安妇问题上,秦郁彦貌似很客观,很公正,很学术,其《慰安妇与战场上的性》一书甚至被吹捧为“慰安妇和慰安妇问题的百科全书”。然而,这本书既有引用没有标明出处的地方,也有数字错误,还有对证人证言的断章取义。显然他在思考慰安妇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焦点不是事实的挖掘和认定,而是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他曾经说过,如果官方承担起对这些女性的赔偿责任,那么满足她们的要求可能使日本这个国家瘫痪。“在此,荒谬绝伦的是,其观点的根据竟然从原则和真相转移到了经济考虑和实利方面。”这样,秦郁彦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就彻底撕下了自己的面具。
中韩两国准备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资料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记忆遗产。对此,日本如临大敌。为了阻止中韩两国,秦郁彦主张日本政府提出建议,修改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将19世纪之后的历史资料排除在记忆遗产之外。这是典型的日本右翼的思维和做法,没有正义和原则,只有龌龊的算计和计谋。在这里,秦郁彦已经从一个学者蜕变成了狡猾的政客。
日本历史学界曾经以实证主义著称,这给了伪实证主义可资利用的空间和土壤。我们并不否认,像秦郁彦这样的学者,曾经在一些实证主义研究上做出了贡献。但是,这并不等于他所有的研究都是实证主义的,更不等于他有权利和资格来界定谁是实证主义,谁不是实证主义。事实上,在许多关键而重要的问题上,秦郁彦就是打着实证主义的幌子,混淆视听,招摇撞骗。毋庸讳言,日本政府、右翼势力正是看重其所谓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招牌,借用他的学术光环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他成为舆论界的红人,言论畅行无阻,而且被奉为金玉良言。类似这样的学者,侵蚀和挥霍着前辈学者辛辛苦苦打造的实证主义声誉,也在一步一步地掏空实证主义的精髓。
实证主义,质而言之,就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弄清历史事实;更确切的含义,就是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确界定历史事实所处的位置、所占的比重、所关联的趋势。实证主义在日本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其遭到侵蚀和破坏,这大大影响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
日本的政治形势对学术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更是如此。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根本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学术原则、学术良心的关系?或者说,对于政治层面的压力,学者如何抉择:是逃避,是斗争,还是迎合?有日本学者指出,“勇敢地正视历史上这些不快的事实,才是日本的自豪;不承认过去的非法行为,才是可耻的”。但是,作如此思考的学者,还是少数。正因为如此,日本历史学界近些年形成的学术氛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历史研究开始表现出如下的征兆:缺乏学术根基、缺乏社会根基、缺乏指向真理和道德的根基。如此,历史研究不能不走向衰落,而整个社会的历史意识也就不能不走向肤浅。日本学者北冈伸一指出:“不仅是年轻人,所有日本人对于近现代史的理解肤浅得令人吃惊。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是令人羞愧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
(责任编辑: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