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启功先生求字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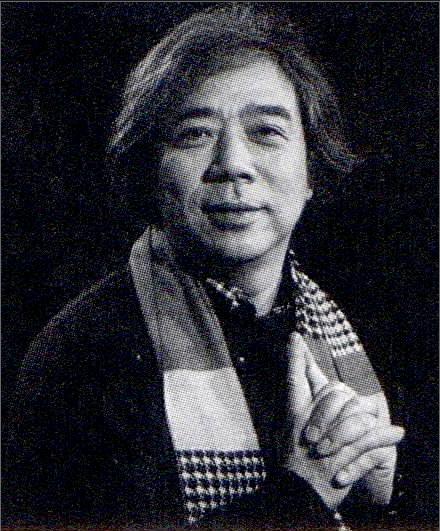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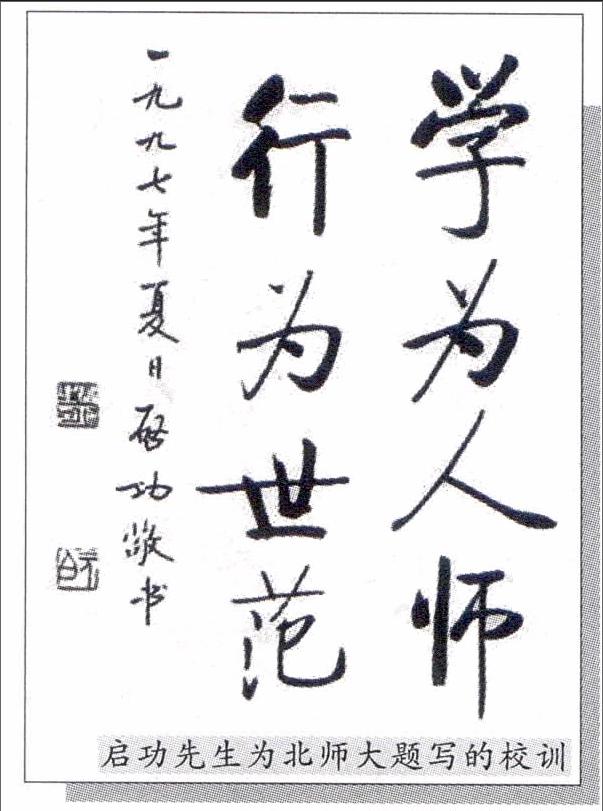
【作者名片】
宋文京,著名书画家、评论家、文化学者,曾任郑州大学教师及《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主编。现为青岛画院专职书画家、理论研究部主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民建山东省委科教文卫专委会副主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篆刻作品曾數十次参选全国书法、篆刻展,并荣膺桂冠,相继在亚欧美澳等地举办巡展。曾出版《艺术不艺术》《一念如剑》《叩问上苍》《千秋文化之旅·中国画》《编辑告白》《中国书香地图》《一字之徒》等多部专著。
【开栏小语】 粗粗算来,从事书画的学习和活动也有40余年了。所历时代从信息匮乏到海量呈现,个人体悟从弯路捷径到大道无门,其间常有阅读和思考,大师的原作拜观过许多,当代的名家见过一些,艺文类书卷天天在读,博物馆实物常常在看,于是便写下许多心得和见闻,“如是我闻”。或曰:读万卷书是知,行万里路是识,我虽行路逾万里,但未读书破万卷,学识知行均有限,不揣浅陋,撰文若干,或叙逸闻,或言史话,或记人物,或谈观感,或抒性情,或录感悟,不拘文体,边读边走边写,艺事共赏,聊备一说。
现在想来,那一次见到启功先生好像很偶然,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却影响了我此后几十年的思想,而且肯定会影响我的一生。
一
1984年我正在郑州大学读三年级,突然被学校选定留校,并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于是我又到北京读了一年书。
次年春天,郑大创办了一份美学报纸《美与当代人》(后改为《美与时代》杂志),我成了首批记者。主编张涵老师知我在北京,就问我能否请一位北京知名书画家题写报头,我答应跑跑看,其实心中很没有把握。
我首先想到了启功先生,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窃以为他是最有资格题这个报头了。
然而,启功先生并不那么好见,据在北师大中文系进修的孙春旻学长讲:由于启功先生身体不好,又加之上门求字者甚多,组织上把他安排在国务院某招待所躲起来了,偶尔回校,猜不准哪天在家。这下麻烦了。
忽一日,北师大中文系一研究生探得“内线”消息,说启功先生这个星期天在家,闻得此信,我喜出望外,觉得这下有戏了。
那会儿我21岁,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到首都也仅是几年间的事,初生之犊,没见过大世面,却有着几分愣而吧唧的胆气,就觉着题字这事已稳操胜券。
于是,便兴冲冲来到北师大内一座幽静小楼,这就是启功先生的“浮光掠影楼”吧。
二
正值午后,我敲开了启功先生家的门,应门的是一位少妇,后来才知道她是启功先生的内侄媳郑喆,她说:启先生休息了。
她话音未落,只听屋内一句京腔京韵的老者声音:“谁找我呀?”随之,一位家常打扮的圆圆脸的老先生便出现了。
我嗫嚅着上前:“您是启功先生吧?”递上介绍信,信上大意是说请启功先生挥毫题写报头之事。
启功边迎我入内边看信,立马表示:“这个我不能写,怎么都找我写呀!我写得又不好——中国书协有一两千会员呢,都写得好,可以找他们写呀!”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局,给晾那儿了。启功一回身,大约是见我尴尬,就说:“您先坐。”我听得真切。后来我才知道,启先生特讲究北京式的礼数,对谁都“您”“您”的。
我坐下后,才看清这间不大的房子是一个客厅兼书房,中间有一不大的案子,房中还坐着两三位和颜悦色的人,甭问,也是来求字的。
我坐下后,便吞吞吐吐地说:“我也是书法和篆刻的爱好者,特别喜欢读您的《论语绝句一百首》。”心下想的是,给启先生一个好学上进青年的印象。
不料启先生说:“我的这些打油诗在大陆还没出版呢,您怎么会读过?”
这会儿我心神已定,说:“我是在北图香港的报纸连载上读到的。”接着我顺嘴背出了四首——“用笔何如结字难……”“题记龙门字势雄……”“少谈汉魏怕徒劳……”“亦自矜持亦任真……”
启先生笑了,很灿烂的笑。他开始讲前些日子去上海留小侄孙子在家的逸事。此刻的启先生神情天真而得意,他的嗓音略沙带哑、发尖,有皇城根底下的老北京味儿。
我心里想,光顺着先生说不行——我的少年意气又上来了,想逆着劲儿试试。我对启先生说道:“你在《论语绝句》中的两句‘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我不敢苟同,我觉得只要是书法法帖名碑,既可师笔又可师刀。”
启先生马上回道:“我这个人觉得碑多为工匠凿拓,加之字口漫漶失真,多不可学,我已七十多了,没时间学了,你们年轻人爱学什么碑什么帖,悉听尊便,只要觉得好,都可以学。毛主席说过: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李鼎铭说得对,要精兵简政,我们就照他的办。”话未说完,又是满堂笑声。
我松弛多了,又与启功先生说了一些有关文字改革、篆刻创新等事情,先生始终谈笑风生。
一段话后,先生走进屋里,旋出,只拿了一本《启功书法选》,对我说:“小伙子,看您是真的在钻研书法,这本书送给您了。”
我喜出望外,赶紧请启功先生签名,他以毛笔签上“文京同志指正 启功”等端丽小字。
继而,先生回身问我:“您刚才让我写什么字来着?”
峰回路转,我忙说是“美与当代人”。
启功先生说:“好,我现在写。”展纸挥毫,他写了一个“美”字,觉得不好,就把那个字从纸边上撕掉了。又说:“我不是不给你写,只是‘美字太不好写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美是大王八。”
在座各位都大笑,问:毛主席还说过这样的话?
先生佯作一脸严肃地说:“你们还别不信,毛主席在庐山美庐前说的,美字可不就是下边一个‘大中间一个‘王上边一个‘八嘛!”
嘿,还真是的。题字旋即写毕了。
又聊,先生那天谈兴极浓,海阔天空,时出妙语,语惊四座。
不知不觉,看天已是黄昏时分了,我起身告辞。
启功先生又写了一个斗方,勉励我写好书法,刻好篆刻,斗方写的是“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
临走我还求了启功先生一幅临写王羲之奉橘帖的条幅,内容是“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向启功先生鞠躬,握别,先生眼中满是笑意。
当晚回到住地,向一起来京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谈了我下午的经历,众人都不相信。
什么?你在启功先生那里得了三幅字和一本书,就一下午?真是天方夜谭!
我拿出实物给他们看,“友邦人士,莫名惊诧”。这回该我笑而不答心下自喜了。
三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得益于偶然中的幸运和丰收,也为我年轻时的轻狂而暗自怀疚。
我不是一个权威崇拜主义者,但通过启功先生,我开始学会尊重那些真正的霭霭长者、谦谦儒者、和合君子,因为在启功先生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天真多于世故的真气在。
启功先生幼年失怙,中年丧妻,老年无子,学历不高,得恩师陈垣先生的指点和破格聘用,后又耕耘不辍,最终成为一代大师。其间苦辣酸甜,挫跌坎坷,自是不计其数,但先生却没有成为“哀哀长空雁,凄凄可怜虫”,而是有着一片晴朗天空般的心胸,他谦和、博学、儒雅有趣、天真烂漫、思维敏捷、不迟滞、不拘泥、不僵化、不自矜、不浮躁,心地如天籁,一任自然,如此道德文章,在当代书坛堪称独步。
启功先生在自撰墓志铭中写道: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子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有如此澄明而豁达的人生态度,先生自有高风亮节和博大宽容的精神。
他曾经称赞郑板桥:“盖其人秉刚直之性而出以柔逊之行,胸中无不可言之事,比下午不可以接致辞,四七所以独绝古今者。”
他也曾盛誉他的先师陈垣先生以及叶恭绰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一片丹诚”,“于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无不拳拳注念”。
先生自己也是这样为人为文,他的博大精深而又明白畅达的思想和艺术,也使他成为人道文道的当代大家。
而且,他还天真,他还有趣,他还招人喜欢,书坛、北师大、文史馆等先生曾工作过的地方,大家都愿意听他笑语,好多的天地人生道理都包含在他如单口相声般的谐谑之中了。
所以,能够有幸与启功先生有一下午的如坐春风般的晤面,面聆垂询诲教,也令我高山仰止、没齿难忘,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后来我又领教了一些自我膨胀而又了无气量格局的艺界、学界之人,与启功先生的谦和逊让形成霄壤之别的是,他们却往往气壮如牛,架子很大。
其实,正如黄永玉《罐斋杂记》中对蚌类的形容一样:“软弱的主人,只能依靠坚硬的门面。”
四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启功先生了。
据说先生家的门上贴有“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的谢客字条,许多朋友、记者、学生都言之凿凿地写入自己的文章中,大家读了都会心一笑,按先生的体貌、地位和幽默習惯,他会这样做的。
但后来,启功先生自己出来说话了:其实,我只在门上的字条上写过这四句话“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可是这字条只贴了一天,就让人给揭走了。我从没称过熊猫,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
这才是启功先生的人格啊!
(责 编 子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