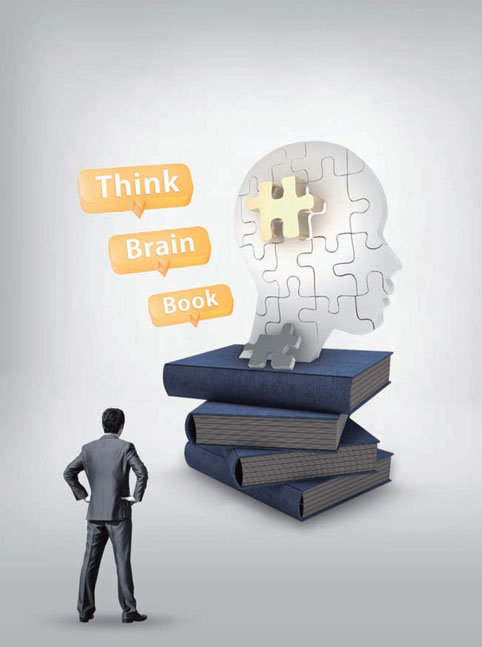从西方青年学者与翻译家看中国出版“走出去”
【摘要】近年来,由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积极姿态与越来越多精品力作的不断涌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对于中国出版物在海外市场的表现,笔者有幸与西方数位领域内专家、学者进行了对话,其中不乏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观察有独到之处,整理成文,供业界同人参考。
【关键词】出版;走出去;西方青年学者;翻译家;变化
【作者单位】宋艳,北京出版集团。
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不断深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出版企业的实力日益壮大。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从图书到企业的“走出去”格局。通过国际书展活动与版权输出等途径,一批国内出版企业在世界图书市场崭露头角,使“走出去”的影响日益提高。同样的,由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积极姿态与越来越多被广泛承认的精品力作的不断涌现,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因工作关系,笔者有幸与西方数位领域内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出版物在海外市场的表现,进行了对话,其中不乏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观察有独到之处,整理成文,供业界同人参考。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变化
十多年来往返于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吴乐思(本名Matthias Wahls,荷兰籍),有着丰富的中国地区跨国出版业务经验,他也十分关注中国出版社参与或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他认为,比起单纯的出版图书,中国的出版社和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出版社不太一样。在版权输出方面,中国的出版社十分积极,尤其在了解哪些书具备输出潜力的时候,会不遗余力促成这桩版权贸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的出版社更加关注提升自身的国际知名度,或者说国际声望,而并不只是版权收益。和以前相比,中国的出版社对于国外出版商的了解有所提高。在版权谈判方面,同等条件下他们更愿意与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签约,这和以前他们认为只要版权输出就“完成任务”的想法大相径庭。但他同样提到,现在只有国内的大型出版机构意识到了这一点,更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尚未达到这样的高度。
在吴乐思看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图书版权走出去。现在很多中国的出版社都会设置版权经理,或是与版权代理公司合作,或是独立部门运营,通过与版权代理联系以及参加具有国际性质的书展,输出自己的版权。不过,单纯的通过图书和国外版权经理的交流会非常局限。
第二个阶段是出版社的影响力“走出去”。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国内的出版机构越来越为人所知,至少在行业内的范围是这样的。但似乎更多的中国出版社比较安于现状。
第三个阶段是能够在国外经营自己的出版社。“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中国出版机构在国外收购出版社,但重要的一点是,购买后应投入自己的人力,调整管理模式。不为买而买,而是加入自己的理念。比如在欧洲或者美国运营的出版社也会低价收购一些公司,引入自己的管理体系,逐渐将其做大。中国的出版社则相反,他们认为,相比国外市场,国内市场还是主要的,他们更倾向于以大价格收购那些具备良好规模的公司,这样在收购后不必大动干戈,可以直接加以利用。我觉得中西方在这点上的出发点不太一样,比如西方是为了商业战略去收购,而中国的出版社可能更看重企业名声,花钱买宣传方式,方向上更直接。所以其收购的资金往往不会成为收购的决定性因素,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从出版社本身出发,要有‘走出去的野心。很多中国的出版社只是希望自己的规模变成最大。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想法。相比而言,西方的出版社更多希望自己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在某一领域成为老大,而不是营业额第一。比如自然(Nature)出版集团,他们就是自然科学学术出版物领域的领导者。做精而非做大,这就是西方出版社之于中国出版社的区别。”
出生在荷兰,现任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中国学院院长兼教授的贺麦晓(本名Michel Hockx)与吴乐思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作为研究中国文学与诗歌方面的专家,他关注的是出版企业作为桥梁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的课题。
贺麦晓认为,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比如实施文化与出版“走出去”政策,开办国际书展等等。虽然举动很多,但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给人留下过于形式化的印象。他认为,这些措施,尤其是中国官方的倡议,着重点更在于“软实力”,官方更倾向于使外界的人士相信中国不只是经济,在各个方面都正在变得更强。这一点从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学术著作的出版上就能看出来,西方也十分需要了解中国在学术研究上的前沿成果。学术本身而言就是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知识求索,学界也一直是以一种国际化的跨文化、种族的身份存在。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有很多联合举措,比如,一些西方大学在中国成立校区,教出的学生非常具有文化宽容性,思维上也更为开放;中国官方在资助本国学生留学海外和国外学生留学中国方面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这一点是值得出版领域学习、借鉴的。孔子学院本身促成中西大学合作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也确实有很多正在为跨文化交流出力的孔子学院,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同样也有部分孔子学院因意识形态目的多过文化交流而备受争议。贺麦晓谈到在2015年红极一时的一档BBC(英国广播公司)节目,在这档节目里,英国的中学引入中国的教育模式,让中国的老师们在英国用中国的方法教英国孩子。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新尝试在贺麦晓看来是有意思的实验。这个节目重要的不是讨论哪种教育体系更优,或者说哪种研究方法更先进,而应该更加重视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从教育到中西方在各个层次的交流。就拿这个节目来讲,我们在最后看到的是学生们自己适应了一种不同于本国文化的教育方式,以及那些努力让自己适应英国教育环境的中国老师们。在节目一开始,他们的理念相去甚远,但到最后双方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彼此进行了很好的磨合。换作学术,更应该重视相互的交流才能让大家更了解彼此。
出生在荷兰的贺麦晓,受到荷兰鼓励学习外语的传统影响,在上初中的时候,除了掌握母语荷兰语,还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五种外语。对于语言的系统学习使他本身对其他语言也产生了兴趣,于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选了中文专业。机缘巧合的是学校还给他提供一整年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在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读中文研究课程的时候,贺麦晓除了中文还有了很多学习有关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机会。后来,贺麦晓逐渐喜欢上了当代中国文学,也逐渐有了建树。通过贺麦晓的经历,我们看到的是交流的优势。
而现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西方很多人视学习中文为一条赚钱的道路,原始的兴趣变为实用主义。因此,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重心越来越集中在了解当代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很少有学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抱有真正的兴趣。“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因为某种原因,集中在研究1976年以后中国的发展上。不仅如此,在教学中,越来越多的西方学生只对学习中文感兴趣,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而不做其他中国相关的研究。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主修贸易、经济或金融,同时辅修中文。这些人中文语言能力非常好,中文说得甚至比我这个中文专业出身的教授流利,但他们的阅读能力却非常薄弱,有些人甚至除了中文,对其他中国有关的知识不甚了解。可以看到,现在的英国,很多学习中文的人的动机,就像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学习英语一样,因为这是一门重要的语言,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提供机会和帮助,而不是抱着非要了解这门语言背后文化的态度。就这一点而言,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责任,我认为需要出版企业通过长期的努力来承担,西方的出版机构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中国的出版企业‘走出去照这个标准看,做得还很不够,缺少独立精神,还要承担文化交流之外的内容。”贺麦晓说。
二、哪些图书更具备“走出去”的潜力
美国人陶建(本名Eric Abrahamsen)曾将王晓波《我的精神家园》译成英文,获得美国笔会(PEN)翻译奖。他翻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英文译本书名改为《跑步穿过北京》)还获得美国NEA文学翻译资助奖。另外,富有中国文学“走出去”经验的陶建还创办了中国文学翻译网站——PAPER REPUBLIC。在他看来,中国有许多图书非常适合西方的口味,尤其是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家。“比如格非,王安忆,阎连科等等,尤其是他们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他们早期的作品,故事情节十分丰富,那时候的他们让人觉得总是在试图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使自己的书写变得有力量。这让人联想到美国20世纪早期的一些作家。比他们年轻的中国作家,我也比较关注,其中阿乙,颜歌,曹寇等人的一些作品,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读。或许这话只能代表我个人意见。他们并不像之前一代的中国作家一样拥有某种力量,但是他们更‘聪明,作品中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陶建谈起中国国内作家如数家珍。
他回忆起自己读的第一本中国作家的书是王晓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此为引,他陆陆续续读了王晓波的其它作品。王晓波也成了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
陶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畅销书在品类上有很大区别。就虚构类而言,虽然畅销书总会集中在几类,但在美国,比较畅销的有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而中国则会倾向于武侠小说,校园爱情与职场小说,很难看出有多少交集。非虚构类的图书差别更大,这类图书往往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文化风格即书写风格。中国的读者会更倾向于自助类与成功类图书,美国读者则更多读一些科普类的。美国市场有大量的《你所不知道的关于xxx的故事》类图书,比如关于盐的、睡眠的,写作风格也比较有趣,讲的都是些常见事物但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出版物。
在谈到中美读者阅读口味时,陶建还分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他认为,总的来看,美国读者群体对中国文学作品还没有产生广泛的兴趣。曾有一段时间,美国读者对于中国的伤痕文学和与中国“文革”相关的文学作品(学术出版物为主)有过一些兴趣,之后有关性与毒品的《上海宝贝》和《糖》那样的故事也有过短暂的流行,但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其很快又消亡了。现在的美国读者,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可以期待什么,或是想读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大致上说,他们会希望读一些有关当代中国的作品,从中可以知道中国当代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至于具体的作品类型,读者很可能自己也不清楚。总而言之,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并没有特别的关注。而中国主题图书的读者群体,不应只停留在自己的圈子里,无论是华裔还是普通美国人,都会有兴趣点。早期的美国华人会对像《野天鹅》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文学作品特别关注,好像从中可以找到他们曾经的影子,这种题材对普通美国人同样也有吸引力。
相对于中国读者对各类国际、国内图书奖项的关注,陶建也给出了普通美国读者的看法。“奖项本身会对销售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读者和出版商都会关注奖项,而奖项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作家进行评判的重要参照。但除了诺贝尔奖,各国的奖项影响力其实仅限于其国内,就像中国奖项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英语国家奖项的影响力主要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就这一点而言,这类奖项就算在本国以外进行推广,知名度也不够,而且有些奖项中国人尚且存在质疑,更何况本身就抱有偏见的一些国外读者”。
吴乐思同样从事了15年以上学术、教育领域出版工作,曾在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负责中国出版物的引进。他认为,虽然更多的是中国出版社引进国外的出版物,但国外同样对中国出版物有着一定的需求。例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类图书,这类书翻译过来需要花很长时间,国外的出版社没有能力和精力对此类图书进行编辑出版。也有很多西方出版社对汉语教育类的图书越来越感兴趣,自然科学类在西方近些年来也是热门领域,但中国的出版物可能在此方面稍显劣势。
近年来,贺麦晓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方面,比如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中国网络文学的书。在书中,他不仅谈到了中国的文学,还谈到了中国的出版系统和网络管控,以及其他与创新型经济有关的更大的议题。这类图书的参考资料,在他看来还很不够,是未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