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洲:我的内心还很纯净
呼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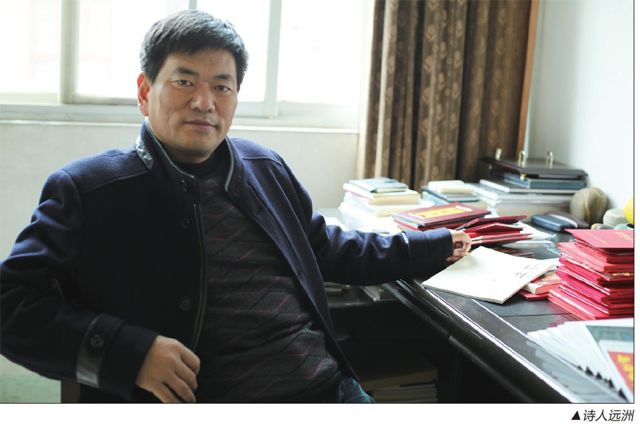
“有什么气质,就写什么样的诗歌”,激情与纯净,朴实与灵动,浪漫与深刻,理想主义与拒绝庸俗,一直是远洲对诗的理解与追求。
这不是个适合写诗的年代,真正的诗人更是稀缺,所幸远洲深居山中,因此内心还很纯净,为诗歌守住一片净土。
远洲将自己正式写诗的时间确定为1988年,这一年他30岁,写了一首130多行的长诗《山里人》。
其实这个在小县城长大的年轻人,已暗地里写了十五年的诗。后来,他将那些他自认为还不能完全称之谓“诗”的文本整理后全部打印出来,装订成了四大本厚厚的《诗草》,收藏在自己的书柜中。
“第一次投稿就能获奖,调动起了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是能写出诗的。”《山里人》写出来后,远洲投稿到《诗刊》,参加了一家酒厂赞助命名的“首届新诗大奖赛”。半年多过去了,石沉大海。原本就是想通过投稿来求证自己是否还是块“写诗料”的远洲,在等待、焦灼、犹豫、挣扎后,正当他要放弃之时,198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单位的门卫递给他一个大信封。“我一看是《诗刊》发来的,还是个大信封,心里一沉,急急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远洲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以为是退稿,可是一摸硬硬的,又觉得有另一种可能。”他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的一个角,露出了一点红色,“心里已经料到是获奖了”。回忆起那个瞬间,远洲依然是一脸的狂喜,似是回到当年一般。
这个优秀奖让躲在无人处的远洲“一蹦老高”,也如同是个印记,仿佛笼罩了他后来的人生之路。
生活在此处
11月丹江边有了初冬的萧杀,远洲家小院里那棵不大翠竹的竹叶发黄了。院子墙上挂着失去了后半截的龙形的根雕,仔细看还是有原来的模样,“诗人总是要找出些诗意的所在”。丹凤县里的文人们是很熟悉这个院子的,而散落在商洛市各地的诗友们也是时常会来这个小院聚集。
远洲家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厚厚的书堆,书堆上摆放着“商洛诗歌学会”和“陕西省诗歌创作基地”两块牌匾。二楼的这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诗人远洲的工作室、书房兼卧室。
“自2003年7月由西安调回丹凤工作以来,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商洛诗歌学会,创办了一本民间刊物《商洛诗歌》。”远洲的历史仿佛都收藏在他睡的那张床下,他能从自己睡的床下翻出四个大档案盒子。两个盒子装有他发表过诗歌的各类报纸杂志,另外两个盒子中,他如数家珍般地从中找出每张报纸、杂志中有关商洛诗歌学会与《商洛诗歌》的报道,连只有三五行的通讯报道都整齐地收藏着。
“《商洛诗歌》现在出版了9期,几乎每期的经费、征稿、选稿、编排栏目、整理及归类电子版都是老师一个人承担。”商洛诗歌学会的诗友周亚娟说,他们眼见着老师为了这本诗集来回地奔波于西安、商州和丹凤。
远洲很骄傲自己主办的每期《商洛诗歌》,能陈列在陕西省图书馆和一些地方图书馆里。“全国有不少民间收藏人收藏馆来函索要《商洛诗歌》。也有诗人把《商洛诗歌》挂在网上出售。”远洲说:“《绿风》曾以专栏形式推出商洛诗歌学会会员作品辑,一次发表了16位诗人的诗作。尤其是今年《关雎爱情诗》夏季刊,一次推出商洛诗人方阵22人作品,还拿出几个整版,推介《商洛诗歌》。”他颇为感慨:一本民间刊物,吸引来全国不少地方诗人的目光,就连台湾地区也有诗人给《商洛诗歌》投稿。“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
远洲自认为自己和几个诗友创立的商洛诗歌学会和《商洛诗歌》,“是对商洛文脉起到了整体的促进作用。”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单个儿写诗,想提高自己找不到门路。”周亚娟说,“现在不定时地聚集进行交流,互相沟通,创作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几乎每个人发稿量都在增加。”她刚刚有两首诗歌发表在《陕西交通报》上,声言要请老师和诗友们吃饭庆祝。
“过两周以后,我就要去西安定居了。”这句话远洲说了几遍。
“远洲老师要去西安定居了。乍一听他说要离开,我有点吃惊,同时我又告诉自己,早就应该料到的。看来,这次他是伤了心地痛,铁了心地要走。”周亚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近期情绪不好,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商山》的审稿、定稿原则和《丹凤文学》的编撰出版上与相关负责人和栏目编辑意见出现分歧,最终选择退出。退出主编一职对于他来说不算个事,但他也许对一些人、一些事重新有了认识,他真的想清静清静了。”
诗是解开锁链的工具
今年56岁的远洲,说话和待人急切而热情,有着一头乌黑粗硬的头发。话到激动处,表情异常丰富。“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他解释说。他的这种激情成就了他的创作。
远洲记忆力惊人,他能清楚地记得当年触动自己写诗的那个“点”。1974年诗人远洲还是一位叫张建民的高中生,在一篇《听英雄讲故事》的作文中,他这样写道:头顶炎红的蓝天,脚踏安然的大地,听着作战的故事,我心早已入迷……
这首诗被语文老师登在学校黑板报的最显眼处,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甚至有女生称他是“未来的诗人”。好奇、踌躇、向往、怀疑、还有种种说不清的情绪开始困扰着这个15岁的县城青年。多年后,回忆起往事,远洲说:诗歌至此就驻在了自己心里。此后他也曾经历过难言的困扰。当第一篇诗歌在《诗刊》的征稿中获奖后,正当他确定自己要走写诗的道路时,突然一段时间,发往各类报刊杂志的20多首诗作没有了下文。“苦闷之时,我又想起了15岁的自己。”更多了一种需要厘清自己的自省与平衡。他觉得:“认清自己,是件极为痛苦和艰难的事。”
56岁,他终于自认为:我是有写诗天赋的。
在1974年的某天,少年张建民在丹凤中学的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赛福鼎·买买提的诗集《鹰》,诗歌中的蓝天、飞鹰、千里草原,无际的意境之美,给这个从小生活在秦岭深处的少年,带来了剧烈冲击,“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这种文本。”
少年的心性是跳跃式的,他也不例外,后来一段时期他又开始爱上《安娜·卡列妮娜》《牛虻》等小说。“这些小说中革命式的爱情是那么的浪漫,我是充满了憧憬和想象的。”远洲讲起这些少年的回忆时,依然激动万分。后来他又开始对素描感兴趣,在他看来自己那时候是在全方位地感受着文学和艺术的氛围,“理想主义的色彩,就是在这个时候树立起来的。”最早迷恋的诗歌反而被推到了一边。
1976年高中毕业后的远洲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成了一名知青,此时,他开始迷上鲁迅的作品,这对他诗歌中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为酷爱读书,他成了一名乡村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在农村的时候,我的诗人梦又开始隐约燃烧起来。”远洲很遗憾搬家时丢失了两个笔记本,那两本里写满了那段岁月的诗歌。
在另一位商洛著名诗人刘知文看来,远洲是有“山村情结”的,“诗中有纯朴的山妹子,有夏夜的稻田,透明的蛙鸣,有质朴自然的农村风俗画,有泥土的馨香。但写黄土地的诗句却这么沉重:背着山爬日子/那是山民遗传的姿势/这千年不移的厚土啊/掩埋的是艰难/生长的是纯厚的禀性
远洲坦诚自己的“山村情结”,是在知青的这个时期形成的。“我躺在无人的山野中,内心自由奔放,那些诗句都是有感而发的真实情感。诗成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对话工具,也成了解决现实锁链的工具。”
诗必须摆脱庸俗化
商洛盛产文人,在远洲看来是极正常的,且不说历史的文脉厚积,单是现在棣花镇出的那位现代大文豪,就足以带动起商洛的文学青年。远洲的老家也属棣花镇,“二十多年以前,因为文学,贾平凹就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商洛籍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
远洲认为,商洛文人能成气候,与商洛处在秦岭深处,“闭塞、安静,不受经济的冲击,鲜少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有关,能潜下心来习文。”“重文轻商”在远洲的商洛诗歌学会中多有反映。他的诗友和学生们散落在丹凤县的各行各业,文友间见面谈论的是谁的诗在什么刊物发表了。
远洲说自己在诗歌面前,永远还是少年时最初的纯净。
1978年底,20岁的远洲被招工到丹凤县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八小时之外,没什么事能做,别人打牌玩乐,我除了看书就写诗。”县城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已经满足不了远洲的“胃口”,他也引起当时的县文化局局长屈超耘的注意。有一年,《工人日报》来组稿,县文化局把丹凤爱好写作的人招集在一起。远洲记住了屈超耘当时对他讲的一番话:“小伙子,要好好写,将来会有前途的。”这对急于想找到肯定的远洲是莫大的鼓励,“我慢慢开始理性地看待诗歌,也开始认真思索自己该如何写诗了。”
1984年县城的法院公开招考法官,远洲通过考试成了县法院民庭的书记员。“法律文书是特别枯燥的,加之有时面对来自上层的压力,法律文书转换了部分的字词后,结果让他瞠目。远洲在这里见识了“玩文字游戏”的厉害,他不愿意悖离自己的正义感。“我找人活动,调到了县志办。”在县志办的两年间,县委宣传部渐渐盯上了这位文笔不错的年轻人。“这条路是能看到底的,给领导写材料,写几年,理论水平上去了,就有可能走上仕途。”应当说,一开始远洲也是很得意这个被县城人们羡慕“有发展前途”的工作。
逐渐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写这种“官方”材料,“强迫自己去写是很痛苦的”。业余时间,他靠大量写诗来排解,诗歌成了他拒绝庸俗生活的手段。
我的内心还很纯净
2005年,《星星》诗刊编辑部发行了“中国·星星诗文库”,远洲的诗歌集《城市泥土》是该文库的其中之一。著名诗歌评论家朱先树给这本诗歌集写了序,“远洲因为爱诗,一直受着诗的诱惑,用他的话来说,写诗改变了我的人生。”
时光荏苒,数年间,远洲在全国及各地报刊发表诗作数百首,并获得各种级别的奖项,已然成为活跃在当今诗坛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而他在《城市泥土》诗作的后记中写道:1992年秋,我带着铺盖卷和诗稿,开始了只身闯荡西安的生活。这个自认“因为诗,我的精神始终年轻饱满”的俗世叛逆者,这一年已经34岁了,他依然坚信“诗意的生活是高质量的生活”,在县城同年纪人不解的目光中,一脚踏上了自认为荜路蓝缕的诗歌之路。
多年来,远洲试着多次问自己一个看似形而上的问题: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答案关乎他的半生努力是否值得,更是他自认过程的反复纵深。
他给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56岁的诗人,提起诗歌时会频繁地使用到一个似乎已经被遗忘的词:罗曼蒂克。当年正是在“罗曼蒂克”的驱使之下,他因诗而去。“我满以为进城后就等于踏进了诗歌的大门,岂料想一切并非我所想象的浪漫。”
这个时期他身处在“诗歌圈子”中,这个圈子是他在最痛苦的时期找到的。1989年他相继给全国20多家报刊杂志投稿,突然都杳无音讯,远洲不得不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个时期我有时整晚在自问自己:是不是做诗人的料?”
迷茫之中,他参加了《诗刊》举办的“全国青年诗歌函授学院”的学习班,一学就是十年。在这个学习班中,他结识了很多全国小有名气的诗友们。
与远洲差不多经历的一群自视为文学青年的年轻人在一起,精神领域的快感,是更容易交叉感染的。做一个纯文学人,成了他最大的追求,“不管谬斯之神是不是肯光顾灵感之门,或者肯不肯轻轻地给予智性的指点,我都忠实地跟着她,仿佛盲人跟着太阳一样,总觉得有一万条金丝线在眼前飘啊飘。”
1992年国家鼓励机关干部停薪留职下海经商,“西安的《劳动周报》看上我的才气”,刚从县宣传部调到县科技局不久的远洲停薪留职到了省城当上了这份报纸的编辑。
面对城市生存竞争的残酷,“我只能暂时卸下诗歌的包袱,在报纸与杂志社之间辗转。”其时,他有两次能进入《西安晚报》副刊的机会,皆失败。“他们招聘的条件其中有两条,必须是西安市的户口,年龄在35岁以下。”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没有省城的户口,等有了省城的户口时,他的年龄已经超过35岁。
1994年冬天,远洲考入陕报集团的《星期天》报,“紧张的编采工作倒还能适应,但最让人头疼的是拉广告,我曾视其为‘逼良为娼,但社长说要‘良也行,但不吃饭不行。”
好在诗歌仍在挽救他的灵魂。1994年5月,《诗刊》社主办的《青年诗人》在太湖举办了一期全国优秀学员改稿会,远洲在这期诗会上认识了邹静之、严力等著名诗人,“全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参加了这次改稿会”。每次与诗友的沟通与交流,被得到肯定后,他心中的诗歌之火,就被烧得更旺一些。
回到西安后,“为了完成广告任务,我不得不向人低头,甚至违心写那些没有文学的报告,日子难挨,茫然惶惑。”好在三年后,他被正式调到《乡镇企业报》任副刊编辑,他终于有了省城的户口。
就在这期间,远洲这个笔名正式开始使用,“地处边远山区,洲喻商州之意”。
2000年前后,全国报刊整顿,《乡镇企业报》停办。“我又开始到处报考各家媒体。”在《金秋》杂志社期间,为了生存,他同时还给两三家杂志社打工。“《新西部》《法制与社会》等杂志社都报考过。”
这种为了生存而丧失了创作激情,不停辗转反侧的生活,让远洲产生了深深的自疑:我的诗歌梦到底在哪里?
“长期动荡,没有职业安全的生存状态下,我的诗歌也只能选择情感真实这个基本点了。”但他坦言:“我的内心还很纯净,表现在诗歌中,就是情感真挚。”
诗人的情怀
走在故乡棣花镇新建的“古镇”街道上,诗人也是一脸的好奇,“这里以前是个臭水坑”,他指着一座新建的桥说。在商洛很多人都认识他。远洲调侃说,自家巷子口的小贩们都知道他是个诗人。
“这是个适合写诗的年代,却不是诗人存在的年代。”去年与他相熟的著名诗人梁小斌病重后的困顿,让远洲唏嘘不已。“这个时代能有太多东西触动诗人的,比如我写的《剪指甲》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讽刺意义。”远洲的这首诗入选了《2013年陕西文学年选·诗歌卷》。
他认为,诗人和诗歌是需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在给予美的享受的同时,诗还是要具有力量的功能。”这力量的功能在他看来就是反映现实生活。当年他看到西安钟楼附近给路人补衣为生的缝衣女:笔挺的先生和鲜艳的小姐/他们的身上不需要扣子/新潮的思想/更容不下你传统的针脚/只有那些远离家门的异乡客,需要缝补一些路途的失落……补衣女/还是返回你们的家去吧/那里有许多破碎的东西/等待你们去细心地缝补
应当说这首诗也暗和了诗人当年在西安的境遇,“城市绝对不是诗的阳光地带”。2003年8月,远洲辞别了省城,自谓:倦鸟知返地重归大自然。再次工作调动也颇费了些周折,好在著名诗人的身份,带给他一点便利,故土是愿意接纳一位文学人才的。
回到家乡后,小城现世安稳,一切静好的慵懒,最是能激起诗人的创作灵性。生性豪放热情,爱结交友人的远洲极为倾慕古代诗人们能云集一起,在山野间纵歌放诗之举。多次在全国参加诗坛聚会后,他想着“商洛有这么多诗人,大家在一起聚会交流也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
“你可以想象一下,5月假期,正在举办丹江漂流节”,远洲兴奋地回忆起2005年5月,“80多个诗人泛舟丹江上,高声吟诗,引得两岸多少的聚焦,这是多浪漫的一件事啊!”后来被媒体称其为首届“丹江诗会”。
此次聚会后,诗人们向远洲提议办一个诗歌学会。远洲并不曾料到,办这么个学会会一波三折,商州竟也有诗人抢着要办。“索性放下了一年多”,直到2008年底,才重拾起此事。
2009年5月30日,“商洛诗歌学会”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艺术创作部命名为“陕西省诗歌创作基地”。牌子后来搁在了远洲家二楼的拐角处。
回到故乡后,他的诗歌创作,以赞美和宣传家乡的山水为主。2011年,长诗《我爱这连绵起伏的山峦》获得第二届中国秦岭生态旅游节“秦岭最美是商洛”诗词有奖征文新诗类一等奖。而他的诗作《有一条河流叫丹江》被谱上曲,在商山洛水间传唱,棣花镇的“贾平凹文学博物馆”收藏了这首歌曲。
“我始终认为,一名真正的知识者,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有责任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小楼内的书虫,一个空有某些艺能的人。我想,一个真正的作家,当他的艺术修为达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他的思想,精神也应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进入不是刻意的,而是自觉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远洲的散文集《在低处》出版后,读者给他的评价。
远洲是网上留下很多踪迹的人,他的新浪博客带给他很多远方的博友,“很多作品也是通过网络让读者熟知的”。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有多首诗作被优酷、派派、56等著名网站朗诵,他笑着说:“我这个山里人写的《钓鱼岛》,在网络的影响最大,很多日本人发到我邮箱抗议。”
他极喜欢一位叫雨音的朗诵家,他的多首诗作被雨音配乐朗诵后,上传到网络上。
“最近几年,越写我越觉得自己陷入一种虚无中”,远洲很不满意自己这两年的状态,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瓶颈期”,写作的量产也在下降,很多时候是将过去的诗作和散文作些整理,再准备出一本散文集和一本朗诵诗集。倒是全国诗歌界的文友们总是请他参加诗会,他也欣然前往。
“这也可能是别人所说的蛰伏期吧,我坚信我是能走出来,而且写作的水平会有一个大的飞跃。”远洲豪爽地笑着说。

